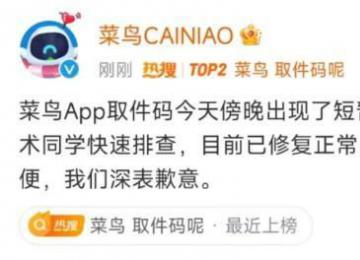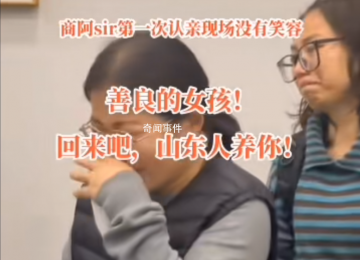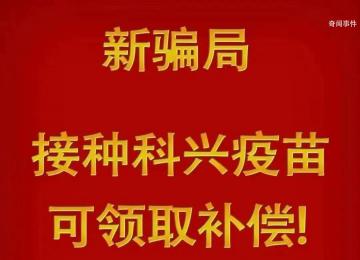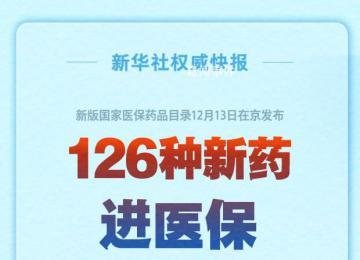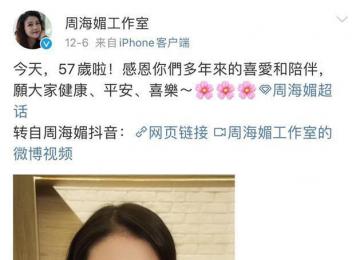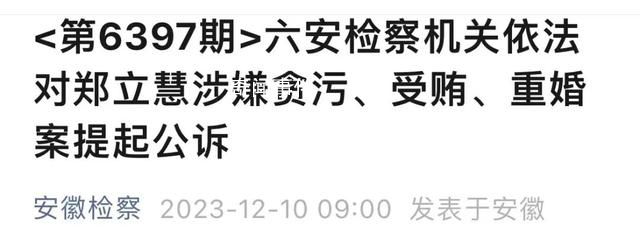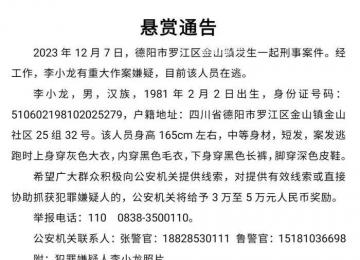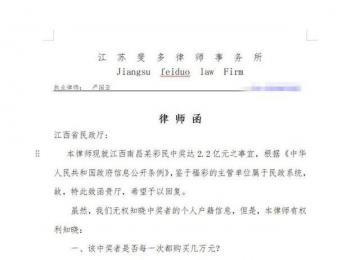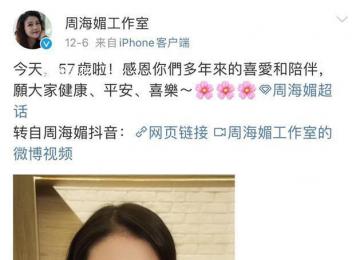端午捕捉蟾蜍的習俗 關于五月捉取蟾蜍的故事有哪些
導讀:我們不得不驚嘆祖先偉大的文化創造精神,可以說今天中國人能夠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生活,能夠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所依靠的正是這種偉大的文...

蟾蜍
可見五月端午捉蟾蜍的習俗在當時不僅流行于民間,連皇家亦不例外。并且皇家連捉蟾蜍也忘不了講究排場,南太醫院的醫官們居然是打著儀仗、鼓吹奏樂去的南海子。這場景,今天想起來都覺得很有趣。端午捕蟾蜍的習俗,今天仍有流行。施立學《關東歲時風俗論》的《端陽采艾》一節,曾對此有生動的描寫:
端陽之晨,山上最難見的怕屬蟾蜍了。老百姓說,什么都有躲人的時候,像農歷七月七日早晨不見飛燕一樣,端陽之晨一般見不到蟾蜍。七月初七的燕子紛紛飛往銀河,成仙人之美,為織女牛郎搭筑鵲橋,蟾蜍干啥去了呢?人都猜它躲起來了。傳說,端陽之晨能捕捉到蟾蜍乃是一幸。此物俗稱癩蛤蟆,往其大肚中塞上墨塊,名喚蛤蟆金,一、二月取出涂用,有解毒療癰、治咽喉腫痛之效。此物耳后腺和皮膚腺的白色分泌物制成“蟾酥”,可供藥用。人說蟾蜍本是月宮之物,月宮別名“蟾宮”,李白《古朗月行》有“蟾蜍飲月影,大明夜已殘”句,猜想月缺月圓乃蟾蜍作祟。科舉時也稱登科為蟾宮折桂。蟾蜍雖然其號不雅,其貌不揚,身上有大小累疣(俗稱癩),但此物生命力極強,可承相當于身體十倍、二十倍的重壓,且有靈性,怕在五月端陽這一天躲起來了。
從漢代算起,五月捉取蟾蜍的習俗,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一年一次的大劫難,蟾蜍們已經過兩千次。如果不是蟾蜍有超凡的繁殖力,并且生命力強,怕早就成了瀕臨滅絕的稀有動物。如果蟾蜍真的有靈,他們應當知道推算人間的歷法,并在五月五日早早找一個安全地方藏起身來。
施文所記載的“蛤蟆金”,在古代文獻中也早有記載,是流傳頗廣的偏方。嘉靖《廣平府志》即記:“取蝦蟆噙墨涂毒瘡。”又同治《宜昌府志》記:東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干取出,涂腫毒有驗”。馮應京《月令廣義》除記此偏方外,另記載了更高級“蛤蟆金”,經過特殊處理后,它竟具有更神奇的力量:
午日取癩蛤蟆,將墨一塊噙其口中,埋于天牢上。七七日取墨收藏。動用有靈。凡涂小兒口瘡,及寫符治瘧止毒之類,皆驗。又夏將此墨涂葫蘆形于壁,則蚊皆聚于內,不蜇人,至早拂去,夜復聚來。
這般下功夫做出的“蛤蟆金”,按照馮應京的記載具有的不是一般的神力。古代夏天苦于蚊蟲者一定不少,所以這樣只要拿來在墻上涂畫葫蘆,就足以讓蚊蟲們聚此不疲、不再侵擾人的墨塊,一定令很多人羨慕并想擁有。羨慕歸羨慕,可這墨塊制造的過程可真很不易。想一下端午日捉到蟾蜍就不易,難度更大的是要埋到天牢。自古“獄不通風”,天牢頂上哪是你隨便去埋癩蛤蟆的地方呢。
史料記載說,蟾蜍呼出的氣有毒。這應當也是有來歷的話。今天在電視的慢鏡頭中,借助高精度的攝像機我們能清楚看到,蟾蜍有很長的舌頭,捕蟲時長舌瞬間吐出又馬上收回,飛蟲已經被卷入口中,成為蟾蜍大快朵頤之物。但這電光石火的瞬間,在肉眼觀察的時代,其實很難看清楚。能看清楚的只是蟾蜍張口,蟲入口中。古人觀察蟾蜍捕食應當也是如此。大概古人就是由此想象,以為蟾蜍是呼出毒氣熏吞百蟲的吧。
上一篇:女子受回南天影響 有家進不了
下一篇:最后一頁
-
 端午捕捉蟾蜍的習俗 關于五月捉取蟾蜍的故事有哪些2024-04-08 17:10:42我們不得不驚嘆祖先偉大的文化創造精神,可以說今天中國人能夠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生活,能夠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所依靠的正是這種偉大的文
端午捕捉蟾蜍的習俗 關于五月捉取蟾蜍的故事有哪些2024-04-08 17:10:42我們不得不驚嘆祖先偉大的文化創造精神,可以說今天中國人能夠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生活,能夠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所依靠的正是這種偉大的文 -
 女子受回南天影響 有家進不了2024-04-08 17:09:12奇聞事件3月5日消息,近日廣東多地進入回南天,室內濕度大增,墻壁、天花板、玻璃等全被水霧覆蓋。甚至廣東江門一名女子因回南天的影響,導
女子受回南天影響 有家進不了2024-04-08 17:09:12奇聞事件3月5日消息,近日廣東多地進入回南天,室內濕度大增,墻壁、天花板、玻璃等全被水霧覆蓋。甚至廣東江門一名女子因回南天的影響,導 -
 回南天能有多離譜 迎春而來到底何為回南天?2024-04-08 17:06:50迎春而來,到底何為回南天?近期,受暖濕氣流影響,我國南方多地開啟回南天模式。網絡上也出現不少回南天門住水簾洞渣‘南’來了
回南天能有多離譜 迎春而來到底何為回南天?2024-04-08 17:06:50迎春而來,到底何為回南天?近期,受暖濕氣流影響,我國南方多地開啟回南天模式。網絡上也出現不少回南天門住水簾洞渣‘南’來了 -
 世界討厭香菜日到了 世界討厭香菜日為什么是2.242024-04-08 17:05:03當我們在元宵佳節之際,沉浸在湯圓、花燈與家人的溫馨中時,或許很少有人知道,這一天同時也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節日——世界討厭香菜日。是
世界討厭香菜日到了 世界討厭香菜日為什么是2.242024-04-08 17:05:03當我們在元宵佳節之際,沉浸在湯圓、花燈與家人的溫馨中時,或許很少有人知道,這一天同時也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節日——世界討厭香菜日。是 -
 90后退休時間可能要延遲到七八十歲2024-04-08 17:03:51經濟人口學家梁建章建議90后延遲退休至80歲,以應對未來養老壓力。網友對此提出質疑和不滿,認為延遲退休應考慮現實情況。解決養老問題需要
90后退休時間可能要延遲到七八十歲2024-04-08 17:03:51經濟人口學家梁建章建議90后延遲退休至80歲,以應對未來養老壓力。網友對此提出質疑和不滿,認為延遲退休應考慮現實情況。解決養老問題需要 -
 看山東吹雪車“硬核除雪”2024-04-08 17:02:282月20日夜間至21日,山東省經歷大范圍雨雪冰凍天氣,據氣象臺降水數據顯示,2月20日14時至2月21日16時,全省16市普遍出現降雪,平均降雪量8
看山東吹雪車“硬核除雪”2024-04-08 17:02:282月20日夜間至21日,山東省經歷大范圍雨雪冰凍天氣,據氣象臺降水數據顯示,2月20日14時至2月21日16時,全省16市普遍出現降雪,平均降雪量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