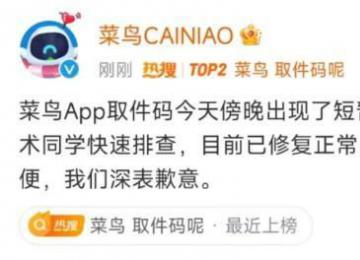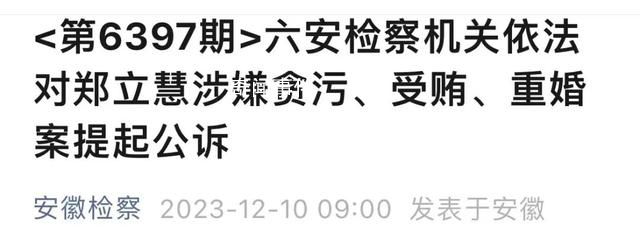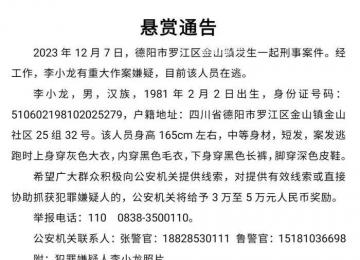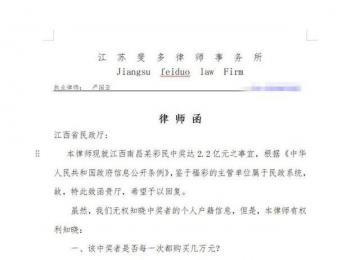大山58歲:不再穿著唐裝作揖拜年
導(dǎo)讀:趕到排練場的時候,大山已經(jīng)出了一身汗,每天中午,他從10.8公里外的家騎車出門,晚上八點(diǎn)半排練結(jié)束,再從排練場騎回去。畢竟要上舞臺呢,...
趕到排練場的時候,大山已經(jīng)出了一身汗,每天中午,他從10.8公里外的家騎車出門,晚上八點(diǎn)半排練結(jié)束,再從排練場騎回去。“畢竟要上舞臺呢,這不能太粗哇”,大山摸摸自己的腰。58歲的年紀(jì),他當(dāng)然不再是30多年前站在元旦晚會上的瘦高小伙子了,金黃色的頭發(fā)已經(jīng)花白,但也并沒有發(fā)福,可他還是堅(jiān)持為了新工作減一減重。

新工作是中文版話劇《肖申克的救贖》,他扮演銀行家安迪在肖申克監(jiān)獄的好友瑞德,也是故事的講述者。一個蹲了大半輩子監(jiān)獄的人,總該要消瘦一些才更可信。他的相聲師父姜昆曾經(jīng)寫文章說,大山對待工作極盡刻苦、認(rèn)真。今天,他似乎仍然如此。
大山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了10分鐘,一直解釋,為什么出來遲了——他上午把自己背好的所有臺詞錄了下來,好在騎車的時候聽,既能更熟悉臺詞,也聽聽自己有沒有什么問題,路上這40多分鐘不能浪費(fèi)。畢竟,中文說得好和能拿中文演話劇是兩碼事。
他現(xiàn)在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鋪在話劇上,笑瞇瞇地憧憬,《肖申克的救贖》應(yīng)該是自己明年最得意的一件作品。
如今的大山,已經(jīng)不再出現(xiàn)在晚會里,盡管那個身穿唐裝或大褂作揖拜年的形象還深深刻在人們的腦海中。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幸運(yùn)地踩中了時代的步點(diǎn),成為一個特別的文化交流符號。是符號也沒關(guān)系,只是,他希望大家別老用舊的眼光看他。
走進(jìn)“肖申克”
“嘩啦啦”,監(jiān)獄大門打開,“新來的”到了“肖申克”。舞臺上一溜站開,不管“老人”“新人”還是獄警、典獄長,一水兒西方面孔。他們一張口,能嚇人一跳,都是地道的中文普通話。看排練前,以為大山肯定是演員里漢語最拔尖兒的,看完發(fā)現(xiàn),他只是最拔尖兒的之一。
“好幾個人是在北京長大的。他們那中文,比我溜。”大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排練場后方的墻壁上,貼著幾個大字:“進(jìn)了肖申克,必須說普通話!!!!”這是導(dǎo)演張國立對所有演員的要求。
大山是第一個敲定的演員。一開始,他有點(diǎn)猶豫,一群外國人用中文演話劇,史無前例,“該不會是變相的‘漢語橋’吧?”30多年前,他出名的1989年,中國的國門打開還不久,洋人能把中文說利索,還會說“蓋了帽兒了”,那簡直就是新聞。“今天不能再演那樣的節(jié)目了,時代變了,我也變了,不能現(xiàn)在上了臺還是給大家來段繞口令啊。”后來聽說導(dǎo)演是張國立,又是龍馬社的項(xiàng)目,還是經(jīng)典的戲,他放了心。
從1982年小說問世,“肖申克”的故事已經(jīng)被反復(fù)演繹了40年,這部在絕境中尋找希望的作品無疑是普世的。故事發(fā)生在美國俄亥俄州,一群西方面孔也很合理,剩下的,就是臺詞是否本土化和演員能否準(zhǔn)確傳達(dá)感情的問題。
如何塑造瑞德,大山提出了不少意見,作為故事的講述者,他的旁白充滿文學(xué)性,可是當(dāng)瑞德到了故事里,是不是還這樣文縐縐地說話?“他畢竟是個監(jiān)獄里的囚徒,不是文人,進(jìn)入戲里的時候,和旁白的感覺不能一樣,雖然是一個人,需要不同的處理。”對于細(xì)節(jié),他和導(dǎo)演張國立摳了很久,細(xì)到是不是偶爾可以帶臟字,某句話能不能加“他媽的”。
大量旁白極考驗(yàn)朗誦水平,湊巧的是,大山在之前兩年意外地做了準(zhǔn)備。2020年,疫情把所有人關(guān)在了加拿大的家里,不能去線下演出,大山琢磨著居家能干點(diǎn)什么。那時,短視頻平臺正在興起,他觀摩了一陣海外博主們的內(nèi)容。分享生活他接受不了,“起床,吃早飯,做個咖啡都要拍,不行不行,我沒那么強(qiáng)的分享欲。”和他一樣的跨國婚姻的內(nèi)容他也看過,覺得挺納悶,怎么兩口子都一起生活好幾年甚至半輩子了,講的文化差異還跟第一天認(rèn)識似的?他沒有這樣的段子,也不想暴露家人的生活。評論國際局勢、時事政治更不是他的專業(yè),相比輸出觀點(diǎn),他還是愿意精心準(zhǔn)備好一個節(jié)目,表演給觀眾,讓觀眾評論。
思來想去,他想到了自己喜歡的那些中國古詩詞,而且在以往的演出中,一趕上大段獨(dú)白,他感覺自己的中文還是有點(diǎn)磕巴和生硬,不如趁這機(jī)會好好練練。于是他花錢在家裝修了一個小錄音棚,買了專業(yè)麥克風(fēng),開始錄制。讓他意外的是,喜歡古詩詞的海內(nèi)外網(wǎng)友不在少數(shù),錄制幾條之后,點(diǎn)贊和閱讀量噌噌漲起來,陳佩斯也來給他點(diǎn)贊,這一下鼓舞了他,逐漸又加上配樂,完善視頻內(nèi)容,從2020年夏天開始,一直沒有間斷。
后來,張國立和他開視頻會議的時候?qū)λf,在網(wǎng)上看了很多他的朗誦視頻,話劇《肖申克的救贖》里故事的敘事者瑞德,正好需要這方面的能力。
“真是沒有想到,居家的時候打算在朗誦方面做一點(diǎn)突破,結(jié)果從疫情走出來,這技能居然就用上了。等于天上掉下來一塊餡餅,這得嘗一嘗啊。”2023年11月中旬,大山回到闊別已久的北京。
中文流利不意味著可以勝任話劇表演。進(jìn)入“肖申克”的人,語言是最低門檻,有些演員日常交流很順暢,可是一站上舞臺,念起臺詞,展開表演,語調(diào)就不由自主地不受控制,水平直接下降幾個量級,只能換掉。大山也有壓力,他是劇中臺詞量最大的演員。
與《中國新聞周刊》見面時,大山進(jìn)入劇組已經(jīng)快四個星期,他感覺心里有數(shù)了,盡管張國立說,按百分制,他們才剛達(dá)到35分。不過,所有人都已經(jīng)能夠脫稿,再經(jīng)過一個月細(xì)排,2024年1月4日全球首演時,他相信能給觀眾一個驚喜:“絕對不是賣老外用中文演話劇這么個概念,中國觀眾早過了看外國人說中文就新鮮的時期了,我們是認(rèn)真排出了一個高水平的精品話劇。”
那個洋小伙子
打開大山的短視頻號,最多的評論就是:“童年的回憶”“第一個記得住的外國人”“小時候聽他漢語說得這么流利都震驚了”……大山在線下演出時也調(diào)侃自己,最不喜歡在網(wǎng)上發(fā)自拍照,因?yàn)闀幸淮蠖言u論說:“大山老師您老了。” “老了就老了唄,最可氣的是什么呢?是還非得添那個大哭的表情符號,淚流滿面的那種。”
在很多觀眾的記憶里,大山是第一個登上春晚的外國人,其實(shí)他并不是,他出名的小品《夜歸》出自元旦晚會。1989年新年,不少中國老百姓在黑白電視機(jī)前看到一個無比新鮮的節(jié)目,兩個金發(fā)碧眼的洋面孔操著尚不熟練的漢語出演了一個發(fā)生在東北工廠家屬樓里的故事。身穿軍大衣、頭戴雷鋒帽,張口一句“玉蘭,開門吶,我是大山”引發(fā)現(xiàn)場一陣爆笑的小伙子,瞬間被無數(shù)觀眾記住了,他也因此獲得了一個中國藝名“大山”。
第二年元旦晚會,他又出現(xiàn)了,這回是站在當(dāng)時最知名的相聲演員姜昆和唐杰忠身邊,和他倆一起說相聲。他的中文已經(jīng)利索了不少,憑借扎實(shí)的基本功和自然的表演,再次贏得了持續(xù)不斷的掌聲。此時,他已經(jīng)拜相聲演員姜昆為師,成為相聲傳人里的第一個外國人,開始不斷在全國各地的舞臺和電視屏幕上獻(xiàn)藝。
等他能夠登上春晚,已經(jīng)是1998年,早已家喻戶曉。大山覺得這事挺有意思,很多有特點(diǎn)的節(jié)目其實(shí)都不在春晚,但是大家會在記憶里自動把它們劃進(jìn)春晚,例如郭達(dá)的《換大米》、宋丹丹和黃宏的《超生游擊隊(duì)》以及他自己的《夜歸》。“春晚壟斷了我們對喜劇節(jié)目的回憶,大家總說,記得小時候看你的春晚節(jié)目,其實(shí)他記得的節(jié)目80%不是春晚那一臺晚會上的,我的成名作也沒有一個是春節(jié)晚會上的。”在他眼里,春晚更像是一個頒獎儀式,是對一個人的影響力和知名度的認(rèn)可,可能也因?yàn)檫@種強(qiáng)大的輿論力量,使觀眾把那些美好記憶都與它勾連在了一起。
當(dāng)初學(xué)習(xí)漢語,大山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會在中國取得這樣的成績。20世紀(jì)20年代,大山的爺爺曾在中國的教會醫(yī)院當(dāng)外科大夫,只待了幾年就因?yàn)閼?zhàn)爭爆發(fā)不得不回國,孩提時代的大山因?yàn)閷χ袊钅畈煌臓敔敹鴮@個神秘國度充滿興趣。高中暑假,他到照相館打工,很多顧客是華人,店里也剛好有個華人同事,聽著他們鏗鏘有力的對談,大山覺得有意思極了,跟著同事就學(xué)了起來,后來他才知道,他最開始學(xué)習(xí)的Chinese,是廣東話。
申請大學(xué)時,他順利地被多倫多大學(xué)東亞系錄取,中文老師根據(jù)他的原名Mark Rowswell給他取名路士偉,結(jié)果,名字沒用幾年就被中國的觀眾們改成了大山。他更喜歡這個來自小品人物的名字,因?yàn)楹苡兄袊厣已潘坠操p。更何況,這個名字和家里兄弟們的名字對應(yīng)上了。大山的老粉都熟知這個有關(guān)名字的梗,大山家里一共三兄弟,他排行第二,老大叫Daniel(丹尼爾),一般生活中就簡稱丹(Dan),小他5歲的弟弟叫Benjamin(本杰明),家里人叫他Ben(本),說到這,大山自己都樂了:“我叫Mark多不般配呀,有了大山這個名字之后,我們?nèi)值芙K于成了‘大笨蛋’組合。”
在中國出名后,他的家人、同學(xué)覺得這事挺新鮮,但也都說蠻合理,因?yàn)樗诖髮W(xué)簡直就是中國迷。漢語本來是選修課,二年級時,大山把它改成主修,四處尋找中國留學(xué)生練習(xí),很快,他就成了東亞系有名的高才生,畢業(yè)那年,獲得了去北京大學(xué)交換學(xué)習(xí)的機(jī)會和全額獎學(xué)金。
接下來的故事,也許不能僅僅概括為中國出了一個西方笑星,而是更像一個文化交流現(xiàn)象。年齡漸長后,大山仔細(xì)思索過這個問題的答案:自己到底為什么會一炮而紅?他覺得,大概是因?yàn)閯偤貌仍诹藭r代變幻的浪尖上。“我出現(xiàn)在大家面前的時候,中國剛剛從一個封閉的時代走出來不久,打開大門,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近中國,人們崇尚外來先進(jìn)知識、技能和文化的同時,也有擔(dān)心——我們自己的文化、語言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世界歡不歡迎我?世界是不是也想向我們學(xué)點(diǎn)東西?”這是一種微妙的矛盾心理,在他看來,中國一方面飛速發(fā)展,一方面又帶著數(shù)千年文明歷史,必然會出現(xiàn)這種矛盾,而且,在很多事情上都矛盾,一個外國人如果想要了解中國的事,得先學(xué)會接受矛盾。
“這個時候,有這么一個來自西方先進(jìn)世界的洋小伙子到了我們國家,不僅僅是學(xué)習(xí)語言,學(xué)的還是傳統(tǒng)文化,那這個人的出現(xiàn),說安慰可能太夸張了,但是對于那種矛盾的心理,當(dāng)然是找到了一種平衡。”
想通了這些問題之后,他感覺豁然開朗,因?yàn)樽约旱氖聵I(yè)不僅僅在喜劇,而是在整個文化交流。既然是文化交流符號,那么在一些重要晚會尤其春晚上的作用就很明顯了,盡管不是第一個登上春晚的老外,但從1998年開始,大山四次參加春晚,成為春晚出現(xiàn)最多的老外,在這樣特殊的場合,大山承認(rèn)也不會有什么特別大的發(fā)揮,就讓大家高興、喜慶,抱拳吼一嗓子:“過——年——好!”
相聲和脫口秀
“為什么今天讓我上臺跟大家開個場呢?可能是覺得這場演出缺一點(diǎn)正能量的東西……這是我的主要責(zé)任啊。”今年2月,在多倫多一場脫口秀演出上,大山作為暖場嘉賓,一出場,就先拿自己這個最標(biāo)簽化的一面開涮自嘲,引起觀眾一陣歡呼。
2011年他與孔子學(xué)院的留學(xué)生一起在春晚表演了群口相聲《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之后,就漸漸淡出了電視觀眾的視線。等到2015年大山再次亮相,卻拋開了他所熟悉的相聲表演,帶著脫口秀《大山侃大山》舉辦個人專場。
那時候,脫口秀剛剛在中國萌芽,很多人認(rèn)為脫口秀就是單口相聲。其實(shí),它們有本質(zhì)區(qū)別,單口相聲更多是在表演,內(nèi)容也是相對固定的橋段,講究傳承,而脫口秀相當(dāng)隨意,講述的是個人生活經(jīng)歷和對這個世界的獨(dú)特見解。
在從相聲轉(zhuǎn)到脫口秀的大山眼里,這兩種藝術(shù)幾乎可以說是中西方喜劇文化差異的縮影——相聲有貫口等語言技巧表演,在一些傳統(tǒng)節(jié)目中,觀眾要品評演員的技巧呈現(xiàn),西方喜劇無論形式還是內(nèi)容,似乎都沒有這么高的門檻。對相聲而言,傳統(tǒng)內(nèi)容很重要,觀眾會以藝術(shù)欣賞的眼光看其表演是否正宗,脫口秀關(guān)注的是當(dāng)下,幾乎沒人表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傳統(tǒng)段子。
大山很喜歡相聲,但是一段時間以后,他就清晰地看到了瓶頸。凡是他參加演出的相聲,幾乎形成一個固定模式——權(quán)威的老師帶著外國學(xué)生,要傳授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結(jié)果說著說著,就發(fā)現(xiàn)這個老師其實(shí)一知半解,還不如學(xué)生。錯位是一種經(jīng)典的喜劇設(shè)計(jì),可是一旦這種設(shè)計(jì)無法讓觀眾感到意外和驚喜,就不再好笑。
大山回憶說:“后來連臺詞都有點(diǎn)形成套路,總是‘大山,我來考考你,這你會嗎?’,我就吹牛‘張口就來啊’。‘這小子有點(diǎn)傲了啊,我得考考他。’考來考去,最后無外乎一句‘嘿,他可真行啊’。這套路玩了好多年,越來越跳不出觀眾的想象,我做不到出乎意料了。”
一個“老外”,在中國傳統(tǒng)相聲里,很難扮演別的角色。他有創(chuàng)作的沖動,但相聲的“鋪平墊穩(wěn)”極其嚴(yán)謹(jǐn),題材也有限制,他承認(rèn),寫原創(chuàng)相聲的坎兒,一直沒邁過去。但分享個人經(jīng)歷的脫口秀就容易得多,也自由得多。他開始創(chuàng)作脫口秀段子,在渥太華、多倫多等城市的小劇場里演出,效果相當(dāng)好,觀眾主要是90后,和他的孩子同齡,他的喜劇已經(jīng)至少服務(wù)了兩代人。當(dāng)然,他的表演依舊用中文,演給華人觀眾。
經(jīng)過幾年現(xiàn)場演出,他打磨出了一個60分鐘的成熟專場《大山侃大山》。從頭到尾有完整結(jié)構(gòu),以自傳體講他自學(xué)習(xí)中文以來的有趣故事,邏輯明確,既不同于單口相聲整段講一個故事,也不同于脫口秀的純“散裝”。
有觀眾說他的脫口秀里仍然有相聲的影子,他一點(diǎn)不否認(rèn),“其實(shí)我還是在以相聲表演經(jīng)驗(yàn)和觀眾交流。雖然在舞臺上沒有典型的相聲腔,但長期受相聲熏陶,一站上舞臺我還是這個習(xí)慣。”但脫口秀畢竟還是解放了他,在相聲舞臺上,他必須扮演一個吹牛的角色,美化自己,這條路走到頭就不可樂了。而任何喜劇形式,歸根結(jié)底是要讓大家笑出來,觀眾靜靜地欣賞最后給點(diǎn)掌聲,節(jié)目就失敗了。脫口秀使他終于有機(jī)會從符號里跳出來,拿自己曾經(jīng)塑造的那個完美的形象去開涮、開玩笑,至于效果,場內(nèi)觀眾用超過他表演音量的笑聲和歡呼給出了答案。在某種程度上,這才接近真實(shí)的他,他想讓人們知道,大山并沒有多么完美,也不那么順利。
2017年,他帶著《大山侃大山》參加了全球三大喜劇節(jié)之一墨爾本國際喜劇節(jié),是那年喜劇節(jié)中唯一的中文節(jié)目。代表中文喜劇表演的是一個加拿大人,他感慨這世界“真夠滑稽的”,也讓他覺得盡到了自己的責(zé)任——讓中文幽默藝術(shù)更好地走向世界。這又有點(diǎn)回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橋梁”的意味上,對他而言,這樣的想法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下意識。
這兩年,他又制作了《大山笑友匯》,一場近兩小時的專場演出,把脫口秀、曲藝、音樂和朗誦全部融為一體,他說:“別人來做一樣的演出確實(shí)會感覺很怪,但放到我身上似乎就變得合理了。”因?yàn)闊o論什么形式,總之還是圍繞著語言藝術(shù),當(dāng)然也可以理解為講故事,有他自己的故事,有中國民間故事,也有歷史故事。
由于他的身份和從事的工作,人們喜歡問他中西文化兩者間的分別,但他覺得,時間長了就發(fā)現(xiàn)其中更多的是共性。因?yàn)槎际侨耍诵韵嗤ā1热缢收b的那些古詩詞,很多專家說那是中國人特有的情懷,可是自己一個“老外”,明明也有同感。再比如正在排練的《肖申克的救贖》,一個人蒙冤陷入絕境幾十年,始終沒有放棄希望,中國人也一定會被觸動產(chǎn)生共鳴。
大約正是這樣的基底,讓大山成為兩種文化的結(jié)合體。他還記得第一次去電視臺,那時還沒出名,主持國際歌手邀請賽,當(dāng)時有兩位代表中國參賽的剛剛出道的年輕歌手,一個叫韋唯,一個叫劉歡。從那個年代一路走過來,他自己也覺得蠻不容易的。讓他感到自豪的一點(diǎn)是,最初上電視表演節(jié)目,按理說就是曇花一現(xiàn)的事情,但一步步折騰了30多年,現(xiàn)在也還沒停。
下一篇:最后一頁
-
 大山58歲:不再穿著唐裝作揖拜年2023-12-20 11:43:33趕到排練場的時候,大山已經(jīng)出了一身汗,每天中午,他從10 8公里外的家騎車出門,晚上八點(diǎn)半排練結(jié)束,再從排練場騎回去。畢竟要上舞臺呢,
大山58歲:不再穿著唐裝作揖拜年2023-12-20 11:43:33趕到排練場的時候,大山已經(jīng)出了一身汗,每天中午,他從10 8公里外的家騎車出門,晚上八點(diǎn)半排練結(jié)束,再從排練場騎回去。畢竟要上舞臺呢, -
 多地血液庫存告急 官方呼吁市民助力2023-12-20 11:42:37近段時間以來,持續(xù)的雨雪天氣和‘斷崖式’降溫,加上呼吸道系統(tǒng)疾病高發(fā),我市團(tuán)體獻(xiàn)血及街頭獻(xiàn)血者人數(shù)大幅減少。相反,正值農(nóng)
多地血液庫存告急 官方呼吁市民助力2023-12-20 11:42:37近段時間以來,持續(xù)的雨雪天氣和‘斷崖式’降溫,加上呼吸道系統(tǒng)疾病高發(fā),我市團(tuán)體獻(xiàn)血及街頭獻(xiàn)血者人數(shù)大幅減少。相反,正值農(nóng) -
 張譯:拍《歡顏》是難得的享受2023-12-20 11:41:4312月11日,此前在騰訊視頻X劇場表現(xiàn)不俗的短劇《歡顏》登陸江蘇衛(wèi)視播出,21歲的青年徐天(董子健 飾)又一次踏上了革命物資的轉(zhuǎn)送之路。徐
張譯:拍《歡顏》是難得的享受2023-12-20 11:41:4312月11日,此前在騰訊視頻X劇場表現(xiàn)不俗的短劇《歡顏》登陸江蘇衛(wèi)視播出,21歲的青年徐天(董子健 飾)又一次踏上了革命物資的轉(zhuǎn)送之路。徐 -
 女童玩耍險(xiǎn)被捂嘴拽走 涉事男子被抓2023-12-20 11:40:4712月17日,針對網(wǎng)傳女童獨(dú)自玩耍險(xiǎn)被陌生男子捂嘴拽走一事,福建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發(fā)布通報(bào):2023年12月16日21時許,我局接群眾報(bào)警,稱
女童玩耍險(xiǎn)被捂嘴拽走 涉事男子被抓2023-12-20 11:40:4712月17日,針對網(wǎng)傳女童獨(dú)自玩耍險(xiǎn)被陌生男子捂嘴拽走一事,福建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發(fā)布通報(bào):2023年12月16日21時許,我局接群眾報(bào)警,稱 -
 馬斯克:別從美國進(jìn)口覺醒思想病毒2023-12-20 11:40:01美國企業(yè)家埃隆·馬斯克16日在意大利參加活動時談到所謂覺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馬斯克警告說,(歐洲)不應(yīng)該從美國進(jìn)口覺醒思想
馬斯克:別從美國進(jìn)口覺醒思想病毒2023-12-20 11:40:01美國企業(yè)家埃隆·馬斯克16日在意大利參加活動時談到所謂覺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馬斯克警告說,(歐洲)不應(yīng)該從美國進(jìn)口覺醒思想 -
 俞敏洪:免職CEO與董宇輝無關(guān)2023-12-20 11:38:40東方甄選內(nèi)訌事件告一段落,以CEO孫旭東降級處分為代價(jià),以俞敏洪和董宇輝共同出鏡直播為標(biāo)志,俞敏洪果斷處理了內(nèi)部矛盾,及時平息了喧囂
俞敏洪:免職CEO與董宇輝無關(guān)2023-12-20 11:38:40東方甄選內(nèi)訌事件告一段落,以CEO孫旭東降級處分為代價(jià),以俞敏洪和董宇輝共同出鏡直播為標(biāo)志,俞敏洪果斷處理了內(nèi)部矛盾,及時平息了喧囂 -
 記者實(shí)探東方甄選總部:謝絕訪客2023-12-20 11:37:51東方甄選小作文風(fēng)波持續(xù)發(fā)酵,12月16日,東方甄選在其官方抖音號發(fā)布通知稱,經(jīng)東方甄選董事會決定,董事長俞敏洪兼任東方甄選CEO職務(wù),免
記者實(shí)探東方甄選總部:謝絕訪客2023-12-20 11:37:51東方甄選小作文風(fēng)波持續(xù)發(fā)酵,12月16日,東方甄選在其官方抖音號發(fā)布通知稱,經(jīng)東方甄選董事會決定,董事長俞敏洪兼任東方甄選CEO職務(wù),免 -
 多地倡議節(jié)電:空調(diào)制熱不超20℃2023-12-20 11:36:5012月15日,江西發(fā)文倡議全社會聯(lián)合行動,共同做好節(jié)約用電、錯峰用電。江西省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江西省機(jī)關(guān)事務(wù)管理局等在倡議書中稱,此舉
多地倡議節(jié)電:空調(diào)制熱不超20℃2023-12-20 11:36:5012月15日,江西發(fā)文倡議全社會聯(lián)合行動,共同做好節(jié)約用電、錯峰用電。江西省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江西省機(jī)關(guān)事務(wù)管理局等在倡議書中稱,此舉 -
 雪后剎車無效 司機(jī)一路順滑下坡2023-12-20 11:35:5612月16日消息,據(jù)國內(nèi)多家媒體報(bào)道,雪后一輛私家車下坡剎車制動完全無效,司機(jī)沉著應(yīng)對,一邊按喇叭提醒行人,一邊順滑,最后有驚無險(xiǎn)。專
雪后剎車無效 司機(jī)一路順滑下坡2023-12-20 11:35:5612月16日消息,據(jù)國內(nèi)多家媒體報(bào)道,雪后一輛私家車下坡剎車制動完全無效,司機(jī)沉著應(yīng)對,一邊按喇叭提醒行人,一邊順滑,最后有驚無險(xiǎn)。專 -
 羅永浩:俞敏洪董宇輝直播又是昏招2023-12-20 11:35:0012月16日,董宇輝和俞敏洪合體現(xiàn)身直播間。隨后@羅永浩的辟謠號發(fā)文稱:看了一會兒,覺得觀感很差,又是個昏招。糾正了錯誤,談好了條件,
羅永浩:俞敏洪董宇輝直播又是昏招2023-12-20 11:35:0012月16日,董宇輝和俞敏洪合體現(xiàn)身直播間。隨后@羅永浩的辟謠號發(fā)文稱:看了一會兒,覺得觀感很差,又是個昏招。糾正了錯誤,談好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