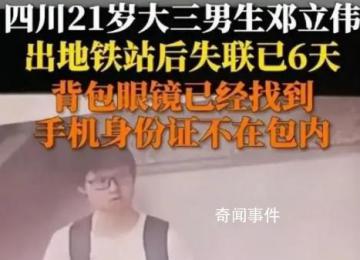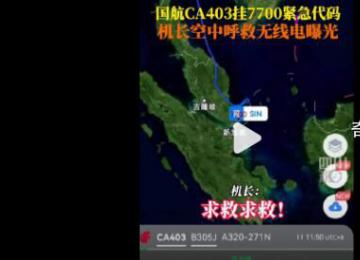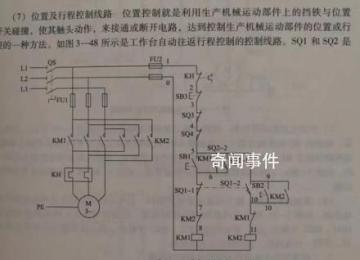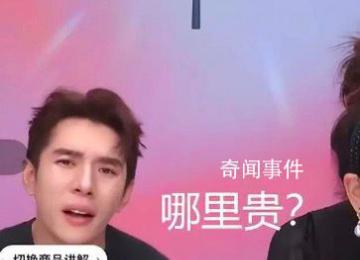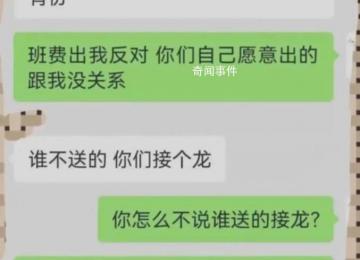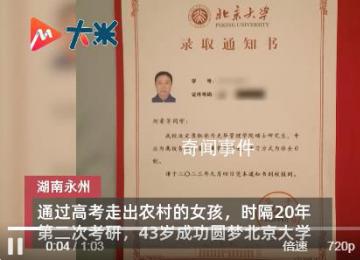上海有安樂死醫院?實為臨終安寧療護
導讀:上海有安樂死醫院?還是全國唯一一家?近日,一篇自媒體文章刷爆朋友圈,提及臨汾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支持安樂死。解放日報·上觀記者求證
上海有“安樂死”醫院?還是全國唯一一家?近日,一篇自媒體文章刷爆朋友圈,提及臨汾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支持“安樂死”。解放日報·上觀記者求證發現,此自媒體文章錯漏百出,借“安樂死”吸引眼球,對“臨終/安寧療護”存在誤讀。文章中大幅內容引自2016年醫療紀錄片《人間世》第四集《告別》,拍攝地是上海市靜安區臨汾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病房。而安寧療護并不等于“安樂死”,上海也不存在“安樂死”醫院。

《上海市安寧療護服務規范》早就明確定義,安寧療護是指通過控制痛苦和不適等癥狀為疾病終末期或臨終患者提供身體、心理等方面的照護和人文關懷等服務,從而提升患者生命質量、減輕家屬心理哀傷,幫助患者舒適、安詳、有尊嚴地離世。世界衛生組織將臨終/安寧療護(Hospice & Palliative Care)定義為一種改善面臨威脅生命疾病的患者及其親人的生活質量的方法,“肯定生命,視死亡為一個正常的過程,既不主張加速也不推遲”。 因此,網傳文章中將臨終關懷描述為“安樂死”、“放棄治療”嚴重背離了安寧療護的初衷。
實際上,上海作為全國唯一一個被整體納入安寧療護試點工作的省市,已實現全市246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覆蓋。近日,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實地走訪臨汾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病房,向讀者呈現這個臨終患者可以安放身心的地方。
如何凝視深淵
臨汾街道是一個很普通的上海社區,老年人密度高,周邊沒有大型商圈,取而代之的是生活氣息濃厚的小店。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臨汾社區醫院”)被密集的小店擁簇,路過時甚至很難注意到。
有30多年歷史的醫院外墻被涂上了粉色,在春日里與櫻花相映成趣。醫院一樓是社區門診,二樓是安寧療護病房區,一共26張床位。作為上海社區基層醫療體系中的普通一員,它卻較早進入了大眾視野。2016年醫療紀錄片《人間世》第四集《告別》播放后,臨汾社區的安寧療護服務為人知曉,以至于一提到它,許多人誤將其與臨終關懷畫上等號。
醫院一樓是社區門診,二樓是安寧療護病房區
《人間世》拍攝組來到臨汾時,醫院副主任胡敏還是一名安寧病房的主治醫生。他記得,醫院一開始有許多顧慮,臨汾能否代表上海安寧療護水平?人們能不能理解或接受安寧療護?醫院作為社會綜合矛盾聚集的場所,紀錄片如何妥善展現?最后,醫院上下都認為,呈現臨終患者在基層安寧療護病房的狀態,是一次讓公眾了解安寧療護服務難得的機會,也是醫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紀錄片見證了71歲放射科退休醫生梁金蘭朗讀最后的手寫信,見證了“文藝大叔”王學文從幾個月到5年生存期的生命奇跡……因為這些臨終患者直面鏡頭的自述,讓更多人知曉安寧療護,思考是否選擇安寧療護。此后,醫院總是能接到來自全國的電話咨詢、籌款資助,甚至招聘員工時,新來的醫生護士都能對臨汾的安寧療護侃侃而談。
很難想象在上世紀90年代,安寧療護仍是一個刺耳、敏感的詞匯。經過30多年的探索,上海安寧療護服務從業者已增長到8000余名,市民對于安寧療護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然而在對經濟欠發達城市地區的調研中,不了解安寧療護的老年群體可達到80%。為了減少文化觀念上的阻力,上海安寧療護的先行者不斷走進社區、校園,開展生死教育,“我們想讓更多人意識到,醫學是有邊界的。跨越邊界就是深淵,當深淵在凝視你時,你如何凝視深淵?”
上世紀90年代,安寧療護仍是一個刺耳、敏感的詞匯
安寧病房是緩沖帶
與一般的醫院病房不同,安寧病房非常安靜。病床旁只有簡單的呼叫按鈕和輸液桿,看不到心電監護、呼吸機,病區內設活動室、讀書角放了一些書籍。
“安寧療護并非外界所說的放棄治療,我們只是不干預疾病本身的治愈性治療,而是針對疾病帶來的痛苦癥狀,做對癥舒緩治療,進行疼痛管理,提高臨終病人的生命質量。例如晚期腫瘤病人腹水、惡心嘔吐、壓瘡等情況,其實都可以避免或大幅度改善。”張敏是安寧病房護士長,在來到臨汾前,她在一家區級醫院重癥監護室(簡稱“ICU”)工作13年。
在那里,她看到很多病人在離世時,氣管是被切開的,身上有7、8根補液管、導尿管、引流管,甚至見不到親人最后一面。一家轉來安寧病房的肺癌病人也曾告訴她,ICU燈光24小時開著,他感到非常煩躁,經常無意識地打到醫護人員、拉扯身上的導管。雖然很抱歉,卻沒辦法控制自己。某天晚上,他的額頭特別癢,但是插著呼吸機無法表達、身體無法動彈,只好硬生生挺了過去,非常痛苦。后來再次被送往ICU前,他下定決心要轉到安寧病房。
“安寧病房讓已無治愈希望的臨終患者從無法喘歇的救治狀態進入緩沖帶。”潘菊美是安寧病房主任,畢業后從長海醫院規培結束便來到臨汾。她說,這里像是一個生命旅程的驛站,臨終患者身上已經千瘡百孔,而疼痛管理和舒緩護理等技術的發展,已經能為他們減輕生理上的煎熬。與此同時,這個“驛站”充分尊重臨終病人的感受和意愿。如果經過止痛、舒緩等手段令患者感到有了“改善”,想聯系開刀醫生或專科醫生再進行積極治療,可以隨時安排轉診。
安寧病房讓臨終患者從無法喘歇的救治狀態進入緩沖帶
不僅是臨汾,上海的安寧療護體系從以社區基層為主體變成了上海各級醫院都在推進,居民基本的安寧療護服務需求已經可以被滿足。在醫護看來,以患者的需求為中心,整合多方資源,推進居家與醫療機構等場景的靈活切換,是安寧療護發展的必然趨勢。
臨終患者不只是病人
檢驗、給藥、治療,這些在常規醫院中最重要的工作退居其次。安寧病房的醫護明白,一切疼痛管理、舒緩護理只是為釋放心靈痛苦騰出空間。由于中國主流傳統觀念中對死亡的避諱,生死問題很少被中國人談起,往往直至死神開始敲門,面對死亡的焦慮、恐懼情緒才傾瀉而出。醫護人員在高強度工作之外,即使注意到了這些特殊病人的需要,也力不從心。這時候,另一個角色——“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開始接棒。
“在中國絕大部分醫療機構,社工并非‘標配’。外界對安寧病房的社工更知之甚少。”趙文薔是臨汾社區醫院唯一的專職社工。表面上,她的工作總是陪在患者身邊“聊天”。但哪位病人不愿意配合檢查,哪位又開始絕食,只有她知道原因。
在她眼中,臨終病人需要被撕下病癥標簽,還原成一個個鮮活飽滿的社會人。只有同理一個“整全”的人,才能判斷其情緒或行為背后的真正癥結,從而為調整醫患之間、患者和家人之間的溝通與相處提供有效建議。
然而現實是,很多病人在進入安寧病房前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這源于親友不知道如何表達,只能通過“善意的謊言”瞞騙。“在不違反倫理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生命末期如何度過,我們要做的就是尊重他們的意愿。但前提是,病人需要獲得充分的信息。在得到充分、真實的信息后,病人如果仍決定和病魔奮戰到底,我們就要尊重他的選擇。如果病人更看重生活質量,那么在安寧療護后,我們要全力支持他做未盡之事。”
社工趙文薔與臨終患者進行面談
在一次次看似隨意的“聊天”中,趙文薔逐漸梳理出患者的人生故事,逐步讓臨終病人將人生的末期轉化為一場“漫長的告別”。他們在實踐中發現,臨終患者多數都希望最后的日子能和親人在一起,完成殯葬、遺囑和對財產歸屬的處理,考慮是否捐獻器官或遺體,和親朋好友相聚一次,完成最后的心愿,并跟所有珍重的人一一告別。
也是家庭避難所
安寧療護病房也是許多家庭的避難所。病房曾遇到一個年輕的臨終患者。在前期治病階段,患者的母親接連遭遇喪父、喪偶,獨自承擔起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照護壓力。為了省錢,母親總是步行買藥買菜,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患者時而嚎啕大哭,時而大發雷霆,也唯有母親一人承受。一時難以分清楚,誰更需要關心。
“在安寧療護的定義中,患者家屬也是服務對象。他們將陪伴患者走到最后,今后也將帶著創傷繼續生活。如果沒有足夠時間撫平情緒,可能進入極不穩定的心理狀態。如何為家屬提供精神、心靈、社會關系的持續支撐,也是安寧療護著重努力的方向。”臨汾社區醫院副主任胡敏提到。
記者在安寧病房采訪時遇到了穿粉色衛衣的石阿姨,她瘦小精干,說起話來總帶著昂揚的語調。“醫生當時判斷我老伴的生存期只有1-3年,我鉚足全力照顧他,沒想到已經活到第17個年頭了。”石阿姨的老伴患有腦瘤,動過手術,3年前摔了一跤從此臥床。她獨自在家照護了一年多,直到累出腰頸毛病才搬來臨汾。剛來安寧病房,護士很驚訝地問,一個人怎么搞的過來啊?阿姨答:“就挺啊,挺過來的。”
安寧病房不僅松綁了她的雙手,還讓她理解了一種新型的醫患關系——以往醫患之間的關系更像是“就事論事”,例行查房完畢就很難再產生交集;在安寧病房,陪伴反而是最重要的工作,“這里的醫生護士隔兩個小時就會看一次病人,社工基本上有空的時候就來。有一次護士長找我談心,待了一個多小時,聊老伴的病情,聊我怎么照顧病人,還有對醫院的看法。”
一些細節更讓石阿姨感到溫暖。老伴是上海市勞模,剛得病時總念叨自己本來還能在干幾年。“五一”勞動節當天,社工專門為他慶祝。最讓石阿姨感動的是,偶然間提及結婚40周年,被社工有心記下,為此策劃了一場紀念活動。老伴開心得不得了,也逐漸釋懷了心中的遺憾。盡管長久陪在病榻邊,石阿姨仿佛忘記了那些疲憊,“現在省出了很多精力,下午還可以接孫子。我也知道了要為自己而活。”
在安寧療護的定義中,患者家屬也是服務對象
日本著名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曾調研日本居家安寧療護的實踐,在《一個人最后的旅程》中,她感嘆:“生和死已然超越了個人意志,人想著要掌控生死,就是不敬畏天地神明。但在有生之年,如果努力,有些事情會有所改變。不辜負上天給予的生命,努力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創造出一個讓很多人(不管有無家人),包括我們自己安心的社會。”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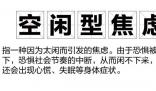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