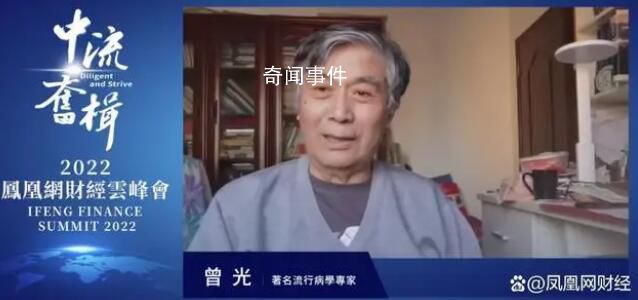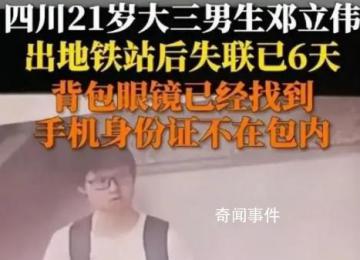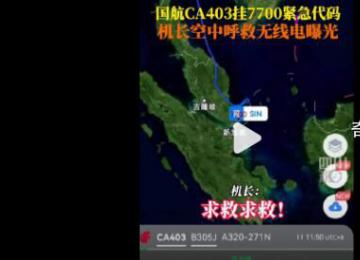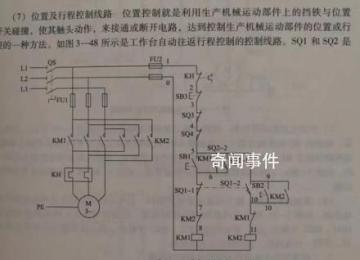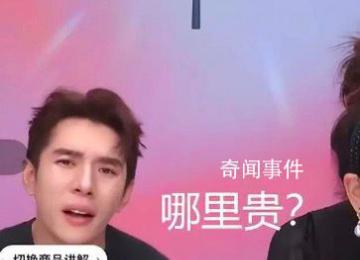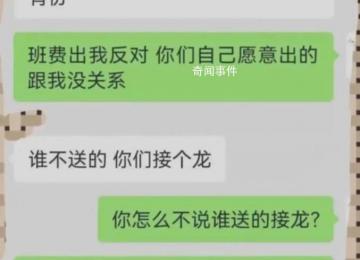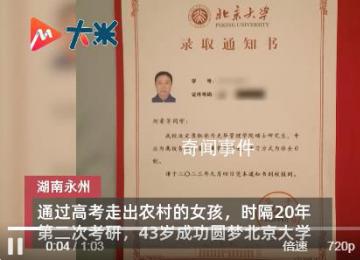無聲的風暴:奧密克戎來過北方村莊
導讀:許多城市相繼迎來新冠感染高峰,經歷購藥和就診困難。我們走訪了河南省、安徽省三個縣城的多個鄉村衛生室,去了解農村地區的基層醫療系統如
許多城市相繼迎來新冠感染高峰,經歷購藥和就診困難。我們走訪了河南省、安徽省三個縣城的多個鄉村衛生室,去了解農村地區的基層醫療系統如何應對沖擊。
眼見為實。在這幾個村莊,感染高峰比想象中更早來到、更早過去。與城市一樣,農村藥物緊缺、醫護人員緊缺。與城市不一樣,農村嚴重缺乏信息,對 “抗原”、對 “奧密克戎”,村民們感到茫然,村醫們開什么藥,他們就吃什么。村醫憑有限的知識、資源和經驗應對。沒有人搶抗原,絕大部分人不知道它。村醫無法知道誰感染了、誰沒有。

在村莊,人人都 “感冒” 了一回,村民蜂擁至鄉村診所,打針、吃藥,直到 “家家都燒過了”,一切又歸于平靜。
感染潮過去一兩周,這些村莊并沒有出現部分人想象的大量重癥和死亡。可一些現狀比預期沉重,它不完全和新冠有關,而是幾十年來基層醫療系統問題的某些體現。
"家家都燒過了"
奧密克戎仿佛從沒來過這些村子,但人人都 “感冒” 了一回。
每個村民都能確鑿地回憶自己是怎么得的 “感冒”:
“干活的時候有點熱,把衣裳解開哩。”
“半夜起來解手凍著哩。”
“睡著覺猛然間冷了,那不就害病了么。”
想要治療 “感冒” 的村民一大早就聚集在村衛生室門前。12 月 22 日早上 7 點 30 分,到了營業時間的衛生室還沒開門。“他們天天可累。” 有人體諒地說。兩個候不住的老人湊上前,“砰砰砰” 拍著卷簾門;另一位回到電動車上,按響車喇叭。“這門上有電話,給他打電話。” 鄰居好心提醒。
“我頂不住了,趕緊開門!” 電話一接通,一位村民立刻喊道。
醫生撩開窗簾一側,從二層的窗戶探頭往下看了看,“來了,來了。” 他說。
衛生室忙碌的一天開始了。涌進門的患者自動分成兩股,一股往右走,迅速把四個床位占上三個,一股往前走,盡量排在藥房窗口最前面。
穿著厚珊瑚絨睡衣套裝,戴著兩層醫用外科口罩,醫生站到他藥房的大桌子前。桌上一半的空間擺著各式各樣的白色藥瓶,他撕下幾張方形的包藥紙,一張一張整齊排好;接著,手指從大大小小的藥瓶上掠過,拎起幾瓶,顛動著抖出幾顆藥:大白片、小白片、紅圓片、綠圓片、棕小片……一張白紙包著一位患者一天的藥,有拎走 4 個藥包的,也有拎走 6 個、10 個的。
等待是衛生室患者們看病的第一步。一般來說,一個村衛生室只有一位醫生,管著全村 1000 多位村民的大病小情。如果哪位村醫像夏曉鈞(化名)那樣,恰好娶了一位上過衛校的妻子,那個村就有了一位護士;如果哪個村的醫生退休了,沒有年輕人愿意接班,他們村就沒有醫生了。
要讓一個醫生在 1 小時內接診 10 位病人,那可是不小的工作量。他要是緊著給排隊的人開藥,打吊瓶的就得被晾著;他要是急著給輸液的扎針,開藥的就得排著。一位年輕的母親披散著頭發,也穿著厚珊瑚絨睡衣,帶著幾歲的小女兒來開藥,等了 20 多分鐘,拎走一塑料袋藥包。一進門就躺上病床的那位老人,也許因為等得太久,腦袋后仰著,鼾聲如雷。
病人們通過相互交流病情打發時間。我咳嗽、我干噦(惡心)、我嗓子疼、我沒胃口啥都吃不下,“頭疼哩跟人夯一頓”。
距離 12 月 8 號 “新十條” 發布已經過去整整兩周,每一天來診所治發燒的人都少于前一天。家家都燒過了,一來就是一家人,沒聽說哪家給落下。從開門到關門,衛生室的病人一直沒斷。
感冒是當地村民每年冬天最常患上的病,大部分人家的房子門對著路,背后就是廣闊的農田,大風一路無阻地掠過土地,從后門灌進去,從窗縫灌進去。村里不通暖氣,男女老少御寒常靠那一身一身的厚珊瑚絨睡衣和用一層層毛氈手工縫的高幫棉鞋。
就像往年冬天一樣,村里人認為天氣冷就容易著涼,著涼了就會感冒,感冒了就去診所瞧病,開藥、打針、輸液、回家。只不過他們都能感覺到今年診所里人多了些,排隊久了些,藥貴了些。只有少數幾個村民認為自己確實感染了新冠,一個說:“傳染這么快,反常”。還有一個說:“要不是病毒,身上咋能瓤(渾身沒勁)哩?”
在村莊,很少人知道 “奧密克戎”,也沒人鄭重地提 “新冠病毒”。兩周感染過絕大部分村民后,它逐漸從人們話題里消失了。
每天早上九點鐘一過,太陽把人們從屋里照出來,人們聚集在村里的丁字路口討論村里的大小事,比如羊的價格。一大一小兩只羊,去年還能賣 1700 元,今年就降到 1300 元。
“你為什么沒藥了?”
變化發生前,醫生們多少有些預感。就比如 12 月初那一天,鎮衛生所開例行視頻會議時,院長對著幾十位村醫模糊地說:“大家再堅持幾天。” 村醫們都已經給村民做了 100 多輪核酸檢測。
從這句話里,村醫賀領會到了領導的暗示——再堅持 “幾天”,那就是 “沒幾天了”。
村醫鄭勝山(化名)從每天的工作中感覺到防控政策在松動。11 月的最后幾天,他給村里人做完核酸,像往常一樣把 “管” 送上去,兩天之后,大家還掃不出核酸結果。他感到異常。他很難確切的地回溯 “放開” 的消息是怎么抵達他的診所,也許是從抖音上看別人說的,也許是誰把鄉里的消息帶進村了,也許是村里被封著的那家超市突然開門了。
村醫羅瑞安(化名)醫生獲得的依據就比較具體,12 月 7 號晚上,鎮衛生院的群里發來通知:明天核酸不再做了。“第二天俺莊誰檢查出來陽性也沒叫隔離,這不就是解封了嘛!”8 號一早,他把之前鎖起來的感冒藥拿出來,擺回到藥房里。
變化落到村醫們具體的工作里,核心變化是:可以收治發熱病人了。
羅瑞安翻出了 5、6 種口服感冒藥,鄭勝山找到了 12 包小兒布洛芬顆粒和百十片撲熱息痛,夏曉鈞的儲備空洞,一片布洛芬都沒有。
之前上邊不允許接治發熱病人,并且隔三差五突擊檢查,查正在就診的病人里有沒有發熱的,看醫生當天的每一張處方,檢視藥房有沒有擺著感冒藥,檢查別的房間是不是還藏著。
因為 “犯不著”,也因為 “擱著過期還賠錢”,醫生們已經很久不進感冒藥了。
起初,他們倒也不覺得之后可能缺藥。誰都認識不少醫藥銷售,有本地的,有外地的,這些銷售人員個個熱情,三天兩頭打來電話問,專程開車或者用包郵的快遞送過來。
幾天后,當他的百十片撲熱息痛開始見底,他才撥通縣里最大的那家醫藥代理商的電話。
“藥都搶沒了。” 銷售說。
對于很多城市里布洛芬和泰諾一片難求的狀況,鄭勝山那時還一無所知,因此那一刻,他沒聽懂那銷售的話。
“啥藥都搶了?你為什么沒藥了?” 他問。
等到他坐車趕到縣里,醫藥銷售公司門口排著一兩百個等著拿藥的醫生。
12 月 10 號以后,來診所的發熱病人越來越多,夏曉鈞每天吃完晚飯就開車出村去找藥。20 號那天下午,眼看藥就要空了,他焦慮地鉆進車里,從晚上 6 點半找到 10 點,跑了六家藥店,一直跑到 30 公里外的縣城。
20 多年村醫干下來,總有幾個關系不錯的朋友,他抱著一點希望,“想方設法也能搞一點回來”。再想方設法也只能買到一兩千塊錢的藥,“這么一小兜”,他指了指墻上給病人裝藥的小薄塑料袋。他先放棄了對布洛芬的希望,后來放棄了對口服藥的,但他的底線是一定要拿到退燒針劑,“只要給人打上針,那也能退燒了。”
68 歲的羅瑞安騎上三輪車進縣城,在醫藥代理公司排了將近兩個小時的隊才買到藥。出發前,他單子上列了 20 樣藥,買回去的不到一半。
藥價一天一漲:有退燒功效的氨基比林針劑原來 7 塊多一盒,漲到 27 元,又漲到 44 元;維 C 銀翹片前一天賣 25 元,第二天賣 55 元;1000 片的撲熱息痛(對乙酰氨基酚片)原來一瓶 40 元,最近一次賣 280 元。
一向了解村民們在治感冒上消費意愿的鄭勝山果斷拒絕了最貴的幾種,他總共要了 60 小盒藥,還擔心自己買多了。回到診所,兩天,藥又賣完了。
病人最多的那天,羅瑞安早上五點被村里人喊起來瞧病,直到晚上十點多都沒來得及洗臉和刷牙,早飯是下午兩點吃的,午飯是晚上十點吃的,忙到雙腿發軟。
病人一個連著一個,先是把輸液室的兩個床位和四個沙發位坐滿了;接著是門廳的 五個沙發位;來輸液的村民漫進小院,五六個人坐在院子里的板凳打吊瓶。他實在分身乏術,只好把沒學過醫但是多年來一直跟著照應診所的妻子喊出來幫忙。“慌得不能行”。村醫妻子回憶那些天,她要換吊瓶、還要 “起針”(把針拔出來)。
盡管夏曉鈞通過加快動作來避免診所出現 “人擠人” 的狀況,他的鄰居還是目睹并只能任由自家門口被病人們的車給堵得嚴嚴實實。
“我們整個縣城都飄著病毒,一出門就能得感冒”
最近村里到底有多少人 “陽” 了,是一個根本回答不了的問題。在農村,極少有人家里有抗原,有的干脆聽都沒聽過,更別說學會怎么用了。對 “抗原”、對 “奧密克戎”,村民們感到茫然。
換成 “核酸”,得到的反應就積極多了——“做了!” 一位頭發白了的老人立刻大聲說。
幾位接受采訪的村醫都沒有主動采購抗原檢測盒。他們無從分辨來就診的病人到底是得了新冠、流感還是感冒,也認為這個時候區分這個毫無必要——“來了就是完全當感冒來治嘛。”
12 月 8 號之前,風聲鶴唳,設卡口,圍鐵皮,家家靜默。“一聽到誰是陽性或密接就嚇得不敢靠近,” 一位亳州的司機說,“你怕我,我怕你。”
12 月 8 號之后,對新冠病毒的恐懼仍然縈繞不去。
村里的一位母親在聽說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兒子感染新冠之后,一宿沒睡著覺。一個住在縣城的中年女士跟外地的家人說 :“我們整個縣城都飄著病毒,一出門就能得感冒。”
河南司機張嘉棟(化名)說他有位好朋友一貫對新冠病毒緊張,隨身帶著酒精噴壺,見別人之前先把自己噴一遍,上車之前把車座椅先噴一遍。防控放開讓他更緊張了。“哎,以后就這樣了,發燒了就發燒吧,想吃藥就吃藥吧。”
一位村醫的妻子誠實地說,放開讓她忐忑,“之前說得很恐怖,不知道到底有多厲害。”
夏曉鈞最害怕家人感染。在做好心理建設后,他把診所門口原來掃健康碼的桌子搬回屋,“再把控,也避免不了了。”
很快,感染就開始了。先是鄉里那些在機關單位上班的,接著是鄉鎮醫院、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再往后就是村里一家連著一家地發燒。羅瑞安當了 50 年村醫,熟悉往年的情況,“傳得這么快,肯定都是陽了”。
村民們都不認為自己陽過了。不僅是出于恐懼可能引發的忌諱,他們中的一些是真的想不通,自己患上的怎么能不是感冒呢?
村民們積極地打疫苗,積極地配合靜默。他們相信,不亂跑,就不會陽。一位在家門口曬太陽的老人說,“我天天就是門前走到門后,哪個能傳到我這兒?” 說這話時,她的兒媳還沒跟她一樣從 “感冒” 中痊愈。
一位做外墻維修的村民也這么想,他手臂上插著針,正在打吊瓶。他雖說天天 “跑著去干活”,口罩天天戴,有意獨來獨往。
“那你咋染上了?” 給他瞧病的醫生妻子在一旁問。
“咋染上了?俺那個小閨女,兩歲多,她可能出去玩了,俺倆睡到一塊了,她給我染上了。” 他說。
“打一針就好了”
為了盡可能保護家人,夏曉鈞在病人最多的幾天穿上了之前做核酸攢下的藍色隔離衣,像理發店給客人倒著穿的、圓領的那種。他沒戴防護面罩,沒戴手套,因為沒有,戴帶兩層醫用外科口罩。睡覺前,他把防護服用酒精噴一遍扔掉,進臥室門前再用酒精給自己噴一遍。可作為護士的夏曉鈞妻子先感染了,她的防護更少。
村民們一有癥狀就直奔他的診所,進了門就熟門熟路地找體溫計,診所的兩根水銀溫度計在病人們之間傳遞。不等醫生開口,病人們就提出要求——“打一針”。
“打一針就好了。”“滴點水好哩快。” 病人們這么說著。要是醫生判斷病人暫時不需要打針,有病人還不高興:“憑啥不給俺打?”
直到醫生們的針扎進肌肉,他們的恐懼、焦慮才能暫時得到平復。
針劑和吊瓶在一些村民心中是最有效的藥物。亳州那位司機沒能給老婆孩子打上吊瓶,很是無奈,診所排隊的人太多了。他對吊瓶的相信源于一些猜疑:“感冒要是吃小藥,得十天半個月才好,如果吊水,兩三天就過來了。” 他說,“吊水用的藥量大,一次就是四瓶。”
發燒、頭疼、惡心、咳嗽、胃口不好,村民們都要求 “打一針”。三個吊瓶從 40 多漲到 50 多,他們咬咬牙,也打。哪怕已經好了,還要再打來一天,“鞏固鞏固”。
維修外墻的那位村民早已退燒,下班后還是直奔診所,打三瓶 “營養針”。吊瓶以氯化鈉或葡萄糖溶液為基底,融合了雙黃連或清開靈針劑。“清熱解毒。” 村里的醫生們這么解釋。打完 “營養針”,他第二天才有力氣干活。
在診所里,一位已經退燒的 70 多歲老人跟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她有心臟病,發燒那幾天她從家里翻出了一盒小兒感冒靈,她看出來那是兒童用藥,于是每頓給自己沖兩條,直到退燒。
這陣子,不少村民在家熬姜蔥紅糖水,有的是從抖音上看的。熬水的大蔥必須保留根須。醫生們也囑咐病程已進入后期的病人回去喝點 “姜糖茶”,還有醫生相信大蒜的功效,“畢竟它里頭也含有抗生素”。
一天,一個隔壁村的人來找夏曉鈞,他吃完感冒藥一直反胃、想吐。夏曉鈞問他,你是不是撲熱息痛吃過量了?病人茫然:我拿的藥量是不小,兩個白丸。
夏曉鈞說,“確實有兩個白丸,但是不是一種藥,一個對乙酰(撲熱息痛),一個安乃近。” 病人把兩種退燒藥一起吃了。
夏曉鈞一貫主張吃藥能好就不打針。最近這半個月給村里人看病,他沒用消炎藥,“因為(新冠)它是一個病毒性的,對不對?”
20 年前,夏曉鈞從大專院校醫學類專業畢業,考到醫師資格證。他們鎮 29 個村將近 60 個村醫里,只有 10 幾個人有跟他差不多的資質。
然而大部分醫生最近半個月里,采用的是和以往治療感冒時一模一樣的方法,既用消炎藥,也用抗病毒藥,雙黃連、清開靈更是常見。
一位醫生曾在幾天前給村里的年輕人治 “扁桃體發炎”(新冠后喉嚨痛),在同一個氯化鈉溶液里同時加了抗病毒、抗細菌感染的藥,吊瓶下到一半多,病人出現過敏反應,血管突出,在胳膊上呈現一條紅線。醫生趕緊停藥,打進抗過敏的地塞米松和撲爾敏,待紅疹消退,醫生問:“還剩點藥,打不打完?”“打完。” 病人說。
幾個小時后,病人被攙扶著回到診所,像 “被電了一樣,一陣一陣地頭暈”,路都走不穩。醫生給病人量了血壓,高壓 162,并叮囑給病人接幾杯熱水喝。
醫生緊急撥通了他好友的電話,縣城里的肝病醫生。醫生用語言把他上午每一步驟操作詳細地重復了一遍,說到最后,他轉頭看向病人:“我給你掛的有沒有黃水的?”
“有一瓶。” 病人說。
他已記不清當時掛的是雙黃連還是清開靈,它們溶解進氯化鈉里時都是淡黃色的。他又給病人沖了糖水喝。
在一線城市三甲醫院內已不太使用的雙黃連和清開靈等中成藥針劑,在鄉鎮診所依然廣泛發揮作用,風險性大、療效不確定的靜脈注射也是如此。村民打的退燒針的主要成分氨基比林也是退燒藥安乃近的主要成分。2021 年 11 月,安乃近片被國家藥品監督局注銷了藥品注冊證書。
農村診所每年都消耗大量吊瓶,全國一年生產近 100 億瓶。2017 年《柳葉刀-全球健康》上的一篇研究提到,中國大約 70% 的感冒門診患者接受了不恰當的抗生素治療,通常是靜脈輸液。中國藥監部門 “限抗令”“限輸令” 多次升級,限制輸液治療。
一個小時內,過敏的病人量了三次血壓,服用了大量糖水,依然眩暈、無力,無法緩解。醫生決定放棄讓病人繼續留觀,建議去縣里。最終,病人父親騎上電瓶車,把兒子馱向縣醫院。
給人看病時是醫生,不看病時是農民
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醫生們一個一個也相繼感染。那是他們最難熬的幾天,但幾位村鎮醫生們沒有一個停診休息。
“確實是硬扛,撐了幾天”,他說,“這幾天確實有一些壓力。”“起熱” 時,夏曉鈞剪了兩包柴胡顆粒,喝下一大碗,后背一陣一陣發冷。
農村的高峰期只有密集的幾天,等到家家都得了一遍,村里的第一波感染高峰就過去了。只有在走訪時,每家診所的床和椅子大都坐著輸液的老人、吊桿上醫生來不及摘下的六七個空吊瓶還能顯露一些奧密克戎造訪村莊后的痕跡。
農閑時節的村莊安靜悠閑。上午太陽高高地升起后,來診所輸液的一位老人叫羅瑞安把只有骨架、沒有坐墊的舊沙發搬到院子里,一邊曬太陽一邊打完三個吊瓶;一個年輕的女士把私家車的副駕駛座位放得盡量平,半躺著,吊瓶支架桿貼著車門,輸液管順著車窗的一條細縫插進她的手背。
羅瑞安終于可以慢下來一點,緩緩講述自己 50 來年作為赤腳醫生的人生片段。他勤奮、刻苦,讀完高中去衛校進修,回來后成為大隊里的村醫。
成為村醫的頭幾年,他背著藥箱在村里給人看病,工資不高,但是飯碗可靠。進入老年,他愛上寫詩,診所里沒病人時,他就拿出筆記本寫上幾行,那些雜糅了古體詩和現代打油詩的一篇篇作品里,充滿了他對于愛情的憧憬,對自然風景、兒女孫輩的稱贊和對自己人生的不滿。
改革開放后,像當年很多大隊村醫一樣,羅瑞安自己開了一家衛生室,從此自負盈虧。這從來不是一份輕松的工作。
每一天,他都壓力重重。不能拒絕任何一位病人,“可能敲門的就是你的大爺、你的晚輩”;也不敢治壞一位病人,那關系到生意和信譽。
診所里正在瞧病的老爺子,手背上的皮膚像牛皮紙一樣又薄又暗,羅瑞安先扎了一針,沒扎進血管,試探地讓老人換一只手。老人極不情愿地伸出另一只,埋怨:“我這輩子叫人扎針,從沒扎過兩次。”
“嗯。嗯。” 羅瑞安仍然低著頭,輕哼了兩聲。
十幾年前,村醫們有了新任務——管理本村居民的健康檔案、慢病隨訪、記錄本村居民的生老病死、寫來自上級衛生院各個項目的月報、季報、年報。怎么也填不完的表格又增添一份辛苦。
羅瑞安打開他臥室里的雙層展柜,一本本統計表格塞滿柜子。50 多歲開始,他學會了使用電腦,連著打印機也是鄉衛生院發的。那些表格就從那打印機里一張張出來。
有一次進縣里送表格,羅瑞安感慨萬千,寫了一段詩:
“鄉村醫生真為難
整天圍著電腦轉
這表那表填不完
要是哪點弄錯了
還嫌鄉醫不沾弦(方言,意為不中用)”
過去一年,基層村醫的大部分是給村民做核酸。每天早上 5、6 點鐘就得出門,先給等著上學的孩子們做,然后是大人,年紀特別大的還要上門服務。羅瑞安騎著他的白色三輪車,在村里這個檢測點做完,再騎到下一個檢測點。
他有時來不及吃早飯。捅喉嚨 4、5 個小時后,感到雙腿發軟。之前鄉里承諾一筆完成核酸檢測工作的薪水,現在還沒拿到。夏曉鈞也沒拿到。鄭勝山的鄉里體諒他們過于忙碌,曾給每個醫生發 600 元 “補貼”。
村醫們給人看病時是醫生,不看病時是農民。他們每個人都有幾畝地。
做了 100 多次核酸,羅瑞安攢了五疊防護服和幾十根咽拭子棉簽,那既是基層醫生辛苦的證據,對他也是珍貴的好東西。他攢下來的一個個靜脈輸液管外包裝就是給病人裝藥的小袋子 ;藥盒里的說明書就是他的包藥紙。“這紙都經過了消毒。” 他裁好、收好那些紙。
他只有 300 元退休金,維持不了生活,因此 68 歲了診所還得繼續經營。他當年就應該當教師去。“我這輩子就選錯了。”
“國家都解封了,咱怕有什么用?也不害怕了”
羅瑞安一輩子都在接受命運和服從命令,這回也是,“國家都解封了,咱怕有什么用?也不害怕了。”
在村里面粉廠打工的老人沒有那么好的脾氣,晚上 7 點多,他急匆匆地進來診所,鞋上、棉襖上、臉上、手上都粘著面粉,等著的半小時里,他控制不住抱怨,“封著不是好好的么,非趕這個時候放!”
他們廠本來有十幾個工人卸車裝面,最近幾天只剩了四個能來上班,剩下的都發燒了,他忍著 38 度的高燒樓上樓下跑,“就應該再封一年!” 打完退燒針,拿了點藥,他又匆忙走了。
沒有哪位醫生聽說村里有人是新冠重癥,倘若真有,家人也會直接送到縣城,診所沒有能力承接。
重癥率低可能是因為疫苗。河南幾個村三針疫苗接種率都很高,有去年就打完的,也有今年 9 月才打完的。打疫苗是強制要求,“你不打,天天給你打電話,一天打幾遍”。一位村民回憶。村民們沒有太多顧慮,“管打疫苗,誰不打?” 另一個村民說,他沒聽說不打的。
另一個原因可能和農村的治病心態以及基層的醫療水平有關。
關于健康,村民們總說,“自己的身體自己知道。” 羅瑞安這么多年聽說也見證了村里不少人查出癌癥,發現時基本都是中晚期。
大病和癌癥治療,農村和城市差別顯著。鄭州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研究員分析了 2015 年河南省 2.6 萬肝癌死亡病例,50-70 歲區間農村癌癥死亡率顯著超過城市。而農村地區也無法即時派出 120 救護車,讓突發心梗、腦梗病人趕上急救 “黃金時間”。
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國家衛健委曾在 2017 年發布《全國各省的平均壽命排行》。北京、上海、天津為代表的大城市人均預期壽命超過了 80 歲,已經是最發達國家的水平。但農村占比較高的省份,人均預期壽命有的還不到 70 歲。衛健委把 80 歲以上的老人列入新冠高危人群。按照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當地奧密克戎期間死亡的 11296 位感染者中,86% 是 70 歲以上老人。
這些數據背后可能是一項事實:很多農村老人并沒有活過容易死于新冠的年紀。走訪期間,沒有哪位鄉村醫生說,村里最近有人死于新冠,不過的確有一兩位老人去世。
一位住在吉林農村的退休老村醫連著四五天半夜聽到村里有人放 “雙響子”,那是當地的習慣,用一陣炮仗送離世的老人最后一程。在寒冷的時節聽到更多 “雙響子”,“是常事兒”。
12 月 22 日傍晚,一位體溫降到 36.8 度的老人倒穿著一個黃大褂來診所打吊瓶,他也想繼續 “鞏固鞏固”。輸液時,在他發呆和昏睡之間,太陽落下去了,夜空布滿星星。診所只剩他一個病人了,比一根手指只粗一點的燈管發著暗淡的白光,外面什么聲音都聽不到。
那天,羅瑞安苦惱于給鎮里提交新冠感染人數的統計表格,他先是在一張白紙上手寫了表頭,然后打開 118 人的微信群,把別的村醫交上去的表挨個看了看,有寫 6 個的,有寫 3 個的,有寫 5 個的。
“寫幾比較好呢?” 他念叨著作出決定,在 “確診人數” 那里寫下了 “4”,提交了上去。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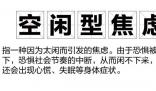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