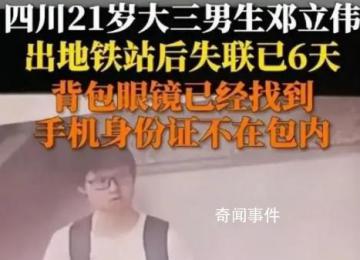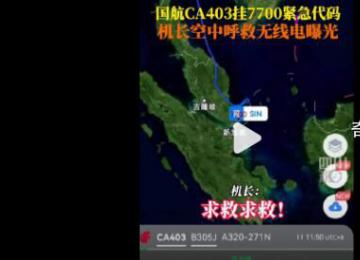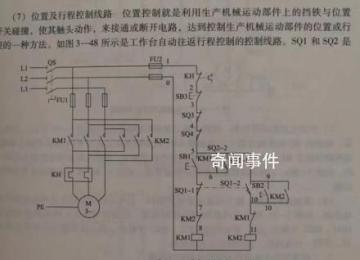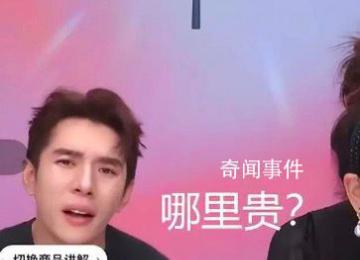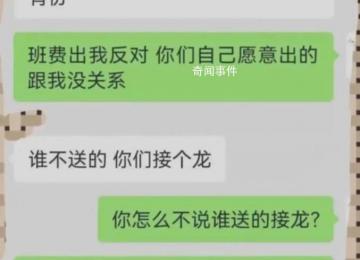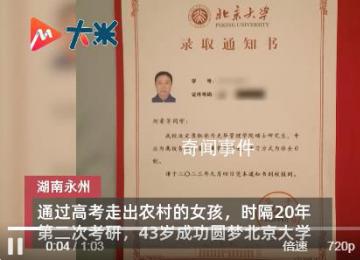月薪3萬 他們卻選擇長期住青旅
導讀:穿過走廊,來到406室的門口,防盜門內時而傳出陣陣歡笑聲,里面似乎正在進行一場派對。然而這里,不是普通的公寓住宅,而是一家青年旅社。

穿過走廊,來到406室的門口,防盜門內時而傳出陣陣歡笑聲,里面似乎正在進行一場派對。然而這里,不是普通的公寓住宅,而是一家青年旅社。
屋內的年輕人,已在這家青旅住了四五年之久。
北漂伊始,他們選擇住進青旅,本是為了節約房租開支,但隨著時間推移,大家的薪資早已不再“囊中羞澀”,有人月入3萬,但依然選擇留在這個“大家庭”中生活。
“長住青旅”,開始成為北漂族一種與眾不同的新生活方式——放棄傳統的租房模式,把青旅當家。
帶著好奇心,我們走近了這群年輕人。
01 長住青旅的年輕人們
周日傍晚,天色還未黑透,位于北京朝陽區東大橋附近的居民樓中,一家青旅宿舍的男男女女已經開始享用專屬他們的火鍋大餐。
客廳里彌漫著濃郁的香料味,食材在兩只小火鍋中翻滾著,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五個年輕住客和青旅老板娘圍著餐桌慵懶愜意地坐成一圈。席間,大家的話題也隨著鍋中熱氣源源不斷地冒出……
住客李鵬背對著電視機,端著蘸料碟,“吐槽”起自己上一周的工作狀態。“上班時間一直有人催著你,問你要東西(文件)。”李鵬皺著眉,言辭中充滿了一種自嘲地調侃。
這位審計師時常會覺得自己像個陀螺,轉個不停。他不經意地用筷子的一端輕戳了一下腦袋,仿佛在表達頭腦已經被工作攪得七零八落。
對面的另一住客王曉嬌順勢加入此番調侃,她用戲謔的口吻描述了不同級別“社畜”的回復模板:“一級‘社畜’回復領導‘收到’;二級回復‘謝謝您,收到’;三級:‘收到領導,我會努力工作的’;終極不管看沒看見,只要收到消息就給對方敲個‘1’。”話音剛落,眾人便暴發出一陣響亮的笑聲。
這時,青旅的老板娘Daisy接上了話茬:“阿姨我都快60歲了,每天在干的也是扣‘1’,只不過是在直播間里。”下一秒,王曉嬌突然又講起一個直播間砍價的段子:農夫山泉的直播間有網友發彈幕說,“你說你是大自然的搬運工。你都搬運大自然了,還跟我要錢?”緊接著,坐在李鵬身旁的住客秦川帶著純正東北口音來了句:“那你給點搬運費唄。”
此時,眾人已笑得發抖。
秦川可以算是幾人中的氣氛擔當,他常常能以三言兩語逗得大家前仰后合。身為計算機工程師的秦川自帶幽默爽朗的性格,這與他的工作所需的一絲不茍形成了有趣的反差萌。
而王曉嬌則就職于一家知名國際教育協會。由于她常常在深夜與海外客戶對接工作,有些日夜顛倒,因此被青旅老板娘Daisy總結為是“中國國籍,美國作息,俄羅斯脾氣,因為當她睡覺時最好不要去叫她。”
由于王曉嬌以最快的速度在北京攢到了近一百萬元,被其他室友戲稱為“嬌總”。而據Daisy介紹,同住一個屋檐下,來自“四大審計事務所”的李鵬,月收入也達到了3萬元,可以和王曉嬌比肩。
王曉嬌對面還坐著一位女住客,飯桌上,多數時候,她都是笑著聽大家聊天,時不時拿起漏勺幫大家夾菜。她就是咖啡師謝麗香,是Daisy開店后的第一批客人之一。
2018年,謝麗香來北京工作時就住在這里,后來遇上疫情,她回了廣東老家,還生了倆娃。今年3月,她再次只身北上,又回到Daisy的青旅長住。“青旅熱鬧一點,自己租房空蕩蕩的。走在一起,都是緣分。”謝麗香說。
坐在最外側的男住客叫張鴻興,是一名環保工程師,去年晉升為部門經理。到9月5日,他已經在這里住滿五年了。
02 不用“押一付三”,老板娘牌“家常飯”只要20元
火鍋依然沸騰著,張鴻興又從身后的小桌上端來一盤苕皮下進鍋里。Daisy此時舉起酒杯,“來,大家干一個。”
對這群年輕人來說,這樣的聚餐雖是家常便飯,但也難能可貴。因為在他們看來,傳統的合租模式僅僅是在房租上的分攤和拼團,大家并不見得真正期待與室友在生活或情感上有任何交集。
因此,像這樣久居青旅、和上下鋪的住客處成家人般的關系,時不時還能組一場熱火朝天的飯局,就顯得愈加特別。
這是一間三室一廳的房子,今年4月份,Daisy才把這里租下來。在此之前,長住客和散客共有20多人,全都集中在附近的老店。眼看著幾個長住的年輕人事業日益騰飛,改善居住環境迫在眉睫。又因為幾個年輕人誰也不愿就此散開,出去獨立租房,于是Daisy決定為他們“升艙”。
在新店,男生住4人間,臥室有兩張上下鋪。剩下的兩個臥室則是女生房,各放著一張上下鋪,都是雙人間。根據房型不同,每月的房費也有2100元和2500元兩檔。
Daisy介紹說,住在青年旅社既不需要“押一付三”,也不需要交水電燃氣費。月付房費、拎包入住,完全免去了傳統租房的煩瑣。客廳、廚房、衛生間等區域和一些家電為共用。除此之外,大家還可以共享一些資源,比如零食架子,每個人都會買一些自己喜愛的小零食擺上去,自由取用。Daisy偶爾也給大家“補補貨”。
每天清晨六點不到,Daisy就會自然醒,然后開始清理垃圾、換洗床單、晾曬衣服、接待客人……
一兩個小時后,大家才陸陸續續起床,錯峰洗漱。除了秦川,其他幾個人的單位都在青旅附近3公里的范圍內。
謝麗香每天騎小黃車上班,七八分鐘就到單位;王曉嬌的單位最近,走路上班只要5分鐘。而秦川,工作單位在海淀,他現在每天的通勤時間都要長達兩個小時……
“趕不走他,秦川已經是我這的鐵粉。”Daisy說,幾年前,秦川在昌平沙河工作時,曾獨自租房小半年,但他很難適應一個人的租住環境。后來,工作又換到了石景山附近,他就決定還是再回青旅居住。
“當時正趕上大冬天,每天早上六點多,天不亮,秦川就要出門趕車。”Daisy看著心疼,曾建議他在單位附近租個房,秦川只輕松地回答:“一個人的時候沒意思。再說這再冷,能有我們東北冷嗎?”
據Daisy的觀察,秦川住在青旅其實也不太常主動和人交流,但他喜歡周圍時刻有人的聲音,“最開始,他睡在上鋪,每天下班回來后就戴著耳機玩電腦,有人講話時,他就默默摘下一只耳機‘偷聽’。”
Daisy就是這樣,她總能細心地關照到每一位住客的起居和情緒。
通常,傍晚5:30左右,Daisy就開始在微信群聊中收集大家的吃飯信息。晚餐19:00開飯,菜單由Daisy決定,人均20 元。報名吃晚餐的人多一點,彩色就豐富一點。
“時間長了我就知道哪些人不吃辣,哪些人無辣不歡。謝麗香喜歡吃紅薯、張鴻興不吃碳水、秦川獨喜歡吃豬耳朵。”Daisy說。
03 不一樣的互動,青旅老板會關心住客工作
在朝夕相處中,長住客們和Daisy從陌生變得熟悉、親密,“他們剛來的時候都帶著一些靦腆,比較收斂,還有一些假客套。”Daisy笑著說,“以前有需求,他們總不好意思跟我提,現在都是直接說:‘阿姨,我衣服脫下來放床上了,你有時間幫我洗一下’;以前吃飯還都客氣地互相讓讓,現在都是‘只顧自己’。”
時針撥回到八年前,Daisy從老家呼和浩特來到北京,陪兒子一起北漂。彼時,她在一家日料店做庫房管理,同時兼管著兩個員工宿舍。
后來,公司解散了,Daisy被委托處理和變賣店內一切辦公用品、設備。也就是在那時,Daisy買下了其中一間員工宿舍,決定做青旅生意,并給青旅取名“New Bee”。
實際上,Daisy做青旅是受兒子在美國留學時的啟發,“我兒子初到美國讀書時未滿18歲,住不了學生宿舍,只能在別人家寄宿,我當時就覺得這種模式挺好,應該是有發展前景的。”Daisy說,
這一點,與王曉嬌當初選擇青旅時的考量不謀而合。王曉嬌在英國留學時,就是homestay(寄宿家庭)模式,也算是青旅常客。因此,開始北漂那年,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便宜實惠又位于市中心的青旅。
Daisy依然記得王曉嬌剛來那天的樣子:“她當時穿著白色短袖和背帶褲,拎著兩個大箱子,站在青旅附近的郵局門口,等我接她。她看起來特別白、特別乖。”
第二天吃飯時,Daisy主動上前與王曉嬌閑聊,得知王曉嬌是陜西咸陽人,來北京是找工作的。
然而,接下來的幾天,Daisy注意到其他住客都會早早起床,打扮好去上班,而王曉嬌卻總是臨近中午才起床。出于好奇和關心,Daisy忍不住問她找工作的進展, “她自己安排得很有條理,今天把在海淀區的幾個公司面試完,明天要面試的公司就都集中在望京。” Daisy說,經過20多天的努力,王曉嬌成功進入了她最心儀的那家公司。
在Daisy眼中,王曉嬌可以說是目前青旅住客中的標桿、勵志的典范,“她經常早晨精神地將丸子頭扎在頭頂,下班回來時累得丸子頭‘掉’到脖子上。”Daisy感慨,“我真羨慕和佩服這些孩子,可惜我生錯年代了,如果能跟上這個年代孩子們的步伐,和他們一起奮斗,該有多好……”
04 鐵打的青旅,流水的客人
五年來,長住客們在“New Bee”找到了一份家的溫暖,也找到了前行的動力。另一方面,Daisy也在這個特殊的社交背景下,發掘了屬于她的陪伴和幸福,以及一些超越年齡的體驗。
去年,秦川曾拉著她去奧體現場觀摩了一場籃球比賽,那是Daisy第一次近距離體驗籃球的熱情和活力。
比賽現場的喊號聲和籃球寶貝的助威勁頭都讓已經60歲的Daisy無比震撼,后來她干脆放開嗓子,跟著秦川一起搖旗吶喊。比賽結束回家后,Daisy聲音已經暗啞,身體也感到疲憊,但年輕人的那股熱血精氣神卻遲遲未散去。
幾年下來,Daisy有無數個像這樣難忘的和年輕人的生活接軌的瞬間。現在,“New Bee”青旅的老店和新店基本都通過攜程、去哪兒等網站接受房間預訂。
據Daisy介紹,目前老店中的住客多數是剛來北京找工作的年輕人和一些暑期工,他們在青旅的居住時間一般不會太長。
不過,Daisy也始終在留心觀察老店的住客,她會把老店里那些優質的、選擇長住的客人“輸送”到新店。“本科嘛是門檻,足夠優秀也能破例。”Daisy半開玩笑地說。
作為青旅的老板娘,Daisy之所以如此在意客人的素質和教育背景,主要是因為,通過她多年的觀察,學歷高一些的年輕人素質普遍也會高,且會更好管理,“和優秀的孩子相處多了,我也能進步。既把錢掙了,還不用太操心。而且通過他們,我能知道很多原本不太關注的事情。”
然而,青旅再溫暖,對于多數人而言,這里注定只是人生中的一個驛站。當住客再次收拾行囊,踏上前方的路途,Daisy難免感到一絲不舍。她會常常寬慰自己:“早晚會有這一天,鐵打的客棧,流水的客人。”
采訪中,Daisy想起了一位外號叫“福哥”的客人,他是這家青旅的第一個住客,在此整整居住了四年零十天。離別之際,這位大塊頭的男生將行李箱往門口一丟,回身緊緊地抱住了Daisy,淚如雨下。
最后,他上了火車,還給Daisy用微信上傳來一段又一段內心獨白的“小作文”。
Daisy打心底里覺得,這些來北京闖蕩的長住客甚至比自己的親兒子陪伴她更多。
Daisy始終對長住客們心懷感恩。猶記得疫情三年,在散客進京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是這些長住客人讓“New Bee”挺了過來。“我們真的是既贏得了機會,也收獲了朋友。”Daisy說。
而在這些長住青旅的年輕人心中,“New Bee”名副其實,也足夠特別。在采訪的最后,秦川又“發話”了:“大多數青旅的老板都是給你辦完手續、收完錢就走了,誰會天天對你噓寒問暖。你在那些地方就只是住客,而這里是我們永遠的‘家’……”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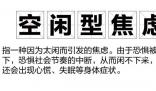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