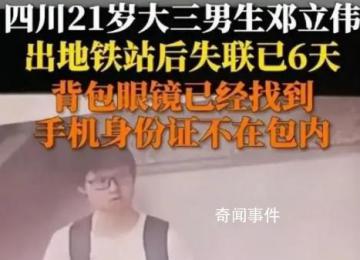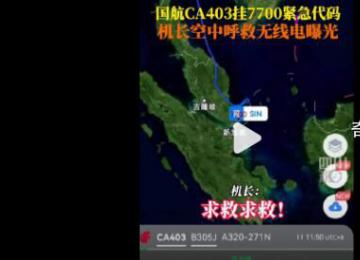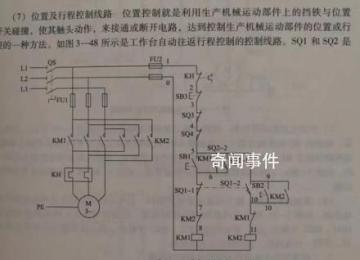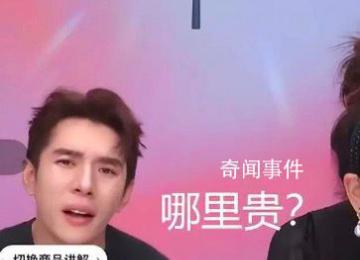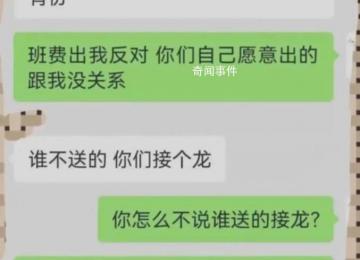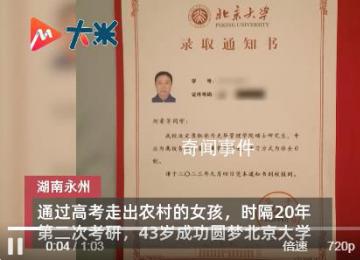胡鑫宇母親:多人曾進糧庫尋找過
導讀:失蹤106天后,胡鑫宇遺體在致遠中學南側金雞山樹林中被發現。據媒體消息,1月29日下午,經家屬同意,警方對胡鑫宇完成尸檢。1月30日上午,
失蹤106天后,胡鑫宇遺體在致遠中學南側金雞山樹林中被發現。據媒體消息,1月29日下午,經家屬同意,警方對胡鑫宇完成尸檢。
1月30日上午,鉛山藍天救援隊的朱先生告訴記者,胡鑫宇失聯后,鉛山縣藍天救援隊曾在學校附近的山上尋找,但沒有收獲。1月份時,藍天救援隊在官方的組織下對鉛山縣的這些山林進行搜索,“但是我們不是說到處亂找,我們是根據他們的安排,是在靠近胡鑫宇老家的一大片山林,我們一直搜索到前天(28日)下午。”

1月30日上午,在胡鑫宇外婆家,紅星新聞記者見到了胡鑫宇的母親李女士。李女士回憶,28日當天晚上,家人告訴她有緊急的事情要去河口鎮處理,但并沒有告訴她具體是什么事。
29日早晨,她接到家人的電話,告訴她鑫宇找到了,一個儲糧倉庫里,用鞋帶“上吊”著,家人去現場看了遺體。
李女士稱,她看到孩子時,遺體已經腐壞,幾乎是“骸骨”,頭顱形狀勉強能看出是鑫宇。身上只穿著一件外套,看起來前后是反著穿的。
有其他家屬稱,發現遺體的附近他們反復找過不止一兩次,但倉庫里面沒有進去過。
紅星新聞記者查閱衛星地圖發現,在致遠中學南側確有一片倉庫建筑物。1月30日上午,紅星新聞記者現場實地航拍發現,確實有幾個大型倉庫,記者還親眼看見警方疑似在側邊一個小倉庫出入,但不能確定是否為事發地。
李女士稱,正如代理律師鄭曉靜所說,錄音筆中可能有關鍵的證據,期待后續公正的調查能揭開事實的真相。
胡鑫宇遺體被發現地附近一糧庫攔起警戒線
另據大皖新聞,1月30日上午記者在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金雞山附近看到,上午十點左右,數輛警車和一輛挖掘機開上金雞山附近,距離致遠中學不遠處一糧庫被圍起警戒線,有疑似法醫和警察在勘察現場。
實地探訪胡鑫宇被發現的樹林:
山路狹窄難攀登,可搜尋范圍較大
1月29日晚,紅星新聞記者來到致遠中學附近進行探訪。晚十點左右,致遠中學門口仍有背著書包的學生以及等待學生放學的家長,門口有警方和特警車輛停放執守。
記者在致遠中學東側發現一條能登上金雞山后山的小路,路旁有些許住戶,不時有背著書包的學生路過。晚十點半左右,能聽到男生住宿學生的打鬧聲。
1月30日,紅星新聞記者來到發現胡鑫宇尸體的金雞山進行實地探訪。記者發現,金雞山可搜尋范圍較大,雖然山勢不高,但有數個山頭,山路狹窄,滿是砍伐過的樹木和荒草,較難攀登。
從學校正門右側一條小路向上走即可進入金雞山范圍,從校門口登上山頂只需要二十分鐘左右。山上林木橫生,滿是灌木叢和樹枝,樹平均高度三四米,較為茂密,地上布滿枯葉和荊棘。
山勢并不高、不陡,從山頂向下俯瞰,能看到致遠中學的教學樓。早六點半,記者聽到了致遠中學的響鈴聲。七點過,致遠中學內響起了學生跑操的音樂。
山上的路較為狹窄,多數地方只有人踩出的痕跡,且路邊不時有溝壑和水坑出現。此外山上有很多刻著碑文的墳地,有的墳上擺著鮮花,有近期祭拜過的痕跡。
而在另一條致遠中學后面的山路上,路則更加難走。山道上布滿了雜草和荊棘,以及被人為砍倒的樹枝,幾近難以下腳,且路時常斷掉,不時需要更換方向行走。
在這一山頭,有工廠的圍墻出現。圍墻內是幾棟廠房樣式的房屋,內有狗吠聲。廠內工作人員稱,胡鑫宇遺體被發現的位置還在山后面。
山路邊的樹木上,有的樹枝有被砍伐過的痕跡,地上也布滿了可能是被搜尋人員砍倒的樹干,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在遠離致遠中學的方向,林木愈發茂密,樹木交枝在一起,難以行走。
后山處廠房外,有一處廢棄的房屋,房屋內堆滿了雜物和垃圾,房屋外仍有較多被砍倒的樹木與雜草,疑似為救援隊員搜尋過的痕跡。
廠房后方的山坡上,樹枝較為荒廢,多為枯木,有放火燒過的痕跡。一路上有很多疑似搜救隊員留下的礦泉水瓶。
金雞山周邊的商家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金雞山附近曾經來過人搜尋,大概有兩三次,去年11月份也來過一次。當時來尋找胡鑫宇的人,攜帶著相關的器械,在山上把灌木叢砍掉了一些,進行了比較細致的尋找,但是沒有結果。
紅星評論
為什么我們如此關注“陌生人”胡鑫宇?
在高中時代,我的一名同班男同學曾在夜半時分突然精神失常至此脫離學涯,而另一名同班男同學也曾莫名失蹤及至被發現溺亡于河塘。那時沒有互聯網,因而這類事件引發的注目,往往抑制于一班、一校范疇內,并不能產生足夠大的影響力。但生命悲厄所造成的沖擊力,并不稍減。
那種唇亡齒寒的悲哀,時隔多年依然清晰。在胡鑫宇事件的疊加沖擊下,我和很多人都能體驗到一種情境:男同學也好,胡鑫宇也罷,他們的命運和我們有著諸多重合之處。正是一種物傷其類的本能而不是獵奇的心理,促使我們關心著他們的下落——在希望未泯時希望他們活下來,在結果出來后又希望以真相還原事件、以強烈的警示和溫情的呵護盡力讓其他人免于沉溺同樣的泥沼。
其實,關注胡鑫宇,就是關注我們自身。這個“我們”包括每個關注者個體、父母、孩子等各種身份。平日里,胡鑫宇是一個普通人,普通到很難被特別關注,可他越是普通越能引人共情。這個15歲少年,背負著家庭的期望和學業的負累、成長的煩惱,如你我一樣。盡管關于他本人并沒有更多的信息提供給我們,甚至一時之間也難以追溯他在過往生活中的更多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身上,有著普通人共有的煩惱與歡欣、困頓。這無疑是值得特別打量、梳理的地方——這個少年到底遭遇了什么,此前發生過怎樣的驚濤駭浪,有必要成為一個社會“解剖”的重點。我們如果希望自己和所喜所愛的人免于絕境,就當然更希望和我們一樣在陽光雨露中冷暖自知的胡鑫宇們自我保全,遠離危險。
個體安全,永遠是社會的底限。這是所有人都須臾不能讓步的目標和意愿,否則我們就會失去談論包括幸福、理想在內的宏大主題的支撐點。
一個未成年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也是社會的。每一個孩子都有健康成長、平安求學的權利。然而,近年來,一些青少年被卷入非正常死亡事件,讓人痛心不已,引發種種關于個體安全的考問。青少年學生處于安全保護體系最完備的環境中,本該是最安全的群體。孩子從溫暖的家庭港灣來到學校,如果因為某些管理環節中的差池,導致個別學生脫離“安全罩”落了單,甚至付出生命代價,令人難以接受,人們就會在內心深處生發出驚詫、后怕、擔憂,從而希望通過對個案的高度重視、持續發聲,促使全社會在方方面面做好基本保障工作,把籬笆進一步扎好。
就此而言,處置這樣一起事件,實際上是在向世人展示一份責任、信心和安全度。而人們對任何細節的打探與分析,與有關方面的一舉一動深度呼應,形成持久的共鳴、互補。這種集體性的情緒、言行,是非常好理解的,也是值得積極回應的。
應該看到,“千人搜山”都未能發現近在咫尺的胡鑫宇遺體,此類情形,使得胡鑫宇事件打上了“蹊蹺”的烙印,從而有“陰謀論”彌漫在胡鑫宇事件之上。某些“陰謀論”固然不科學、過了頭,但客觀上也助推了事件的受關注度。可以說,前期大家對毫無線索可言的少年離奇失蹤有多不解,現在大家對突然之間找到遺體的疑云就有多大,對于及早解疑釋惑的期望就有多急迫。而無有之間的心理反差和失落,也需要撫平和“填補”。
不論如何,全網關注的背后,是社會整體文明程度不斷提升這一實質。人們能夠想見胡鑫宇家人的悲慟場景,也能夠感同身受地提出合乎人性和平安主題的愿望和建議,這是一個社會的“普通心靈”就共同事務表現出的極大關心。這份關心,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集體對遠方的微小的個體生命越來越重視,對人的生命尊嚴越來越尊重——人們從苦苦追問和探尋真相,“倒逼”事件進展加速,到試圖以個案為警醒、警示,呼喚個體安全體系的健全、升級,希望世間再無“胡鑫宇事件”,本質上無不是“命運共同體”意識趨濃的結果。
胡鑫宇已離開我們,而他所留下的所有謎題,都有重新在陽光下“打開”的必要。而最正確的打開方式,還需進一步思索。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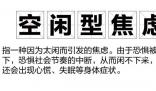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